正视人工智能带来的艺术寻衅_人工智能_人类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创作吗?”正成为一些人焦虑的问题。须要解释的是,每当人们谈起人工智能时,每每想到科幻小说中的强人工智能,它们具有人类一样的情绪和体验,和人类一样生活,看起来彷佛会取代人类;然而,目前我们实际拥有的是弱人工智能,它具备人类一些高端技能,但在情绪、意识等方面与人类差之千里。即便如此,人工智能的进入依然匆匆使我们反不雅观人类自身创作的特点与优长——越是面临技能冲击越要端正和武断本体代价,同时在文艺不雅观念和创作实践上越要有新的打破和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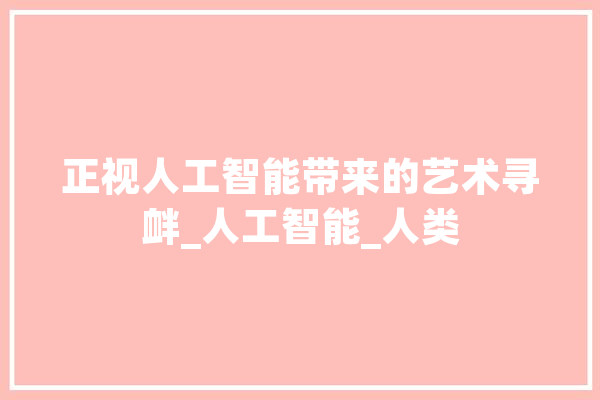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想要成为墨客徐志摩,它须要做些什么?它要拥有徐志摩的阅读量,最大限度靠近他的创作素材;其次,它要学习徐志摩同时期其他墨客的诗,由于徐志摩的诗歌特色是在与其他墨客诗歌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必须节制当时其他墨客的特点,才能更好凸显徐志摩的诗歌特质。但这样,它就能创作出徐志摩的诗了吗?
不,它还短缺一样东西,那便是徐志摩的人生经历。所谓“功夫在诗外”,无论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还是“最是那一低头的温顺,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无不来自墨客自身的平生境遇。人工智能只有具备徐志摩的人生经历,还原他的所有体验,才有可能真正创作出类似徐志摩的诗来。我们读杜甫的诗很冲动,是由于他的诗与他坎坷困顿的人生经历联系在一起;我们听贝多芬的音乐很冲动,是由于他的音乐是他与悲剧命运抗争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如果人工智能创作出杜甫的诗和贝多芬的音乐,但背后没有思想和情绪,我们如何欣赏它、解读它?
没有人生,我们无法理解诗和艺术。人工智能正是在这里遭遇滑铁卢。据研究,只管人工智能具有令人炫目的高超技能,却很难模拟人类基本、无意识的直觉,这被称为“莫拉维克悖论”。它可以轻易学会下棋,但一个婴儿都可以做到的感知天下,人工智能却须要花费大量韶光和困难演习,乃至即便如此也未必学会。文艺创作便是这样一座人工智能很难翻越的山峰。创作并非仅仅是遣词造句,它建基于生命体验之上,来自人生境遇和内在情绪,基底是全体人生和人所处的全体天下。在形式层面,人类未必会比人工智能厉害,但是将形式与生命体验深切关联在一起、创造出更幽美、更有冲击力的作品,人工智能没法与人类比较。这是人类创作的不可替代性,是人类创作的真正肃静。
正如有人所说,机器人写诗不是要代替人写诗,而是帮助人把诗写得更好。人工智能和人类在创作上各有利害,主要的不是孰优孰劣,而是如何发挥人工智能浸染,帮助我们提升创作品质和水准,让人类创作为虎傅翼。就像以往每一次技能改造都将推动艺术创作改造一样,这一次,我们得到了一个比以往所有工具都更强大和更方便的工具。它将重塑艺术创作格局,也将重塑我们对艺术的认识和理解。从长远来看,这场巨变难以避免。
人工智能来了,不仅仅带着它的作品来了。我们刚刚踏上这条道路,刚刚打仗到人工智能艺术创作,尚未思及深层问题。但毫无疑问,在不久的未来,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会对我们的不雅观念和实践带来越来越多的寻衅。正视寻衅,在寻衅中发掘代价、捉住机遇,必将带来文艺创作的新变革新收成。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通报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缺点或陵犯了您的合法权柄,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感激。
作者:卢文超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