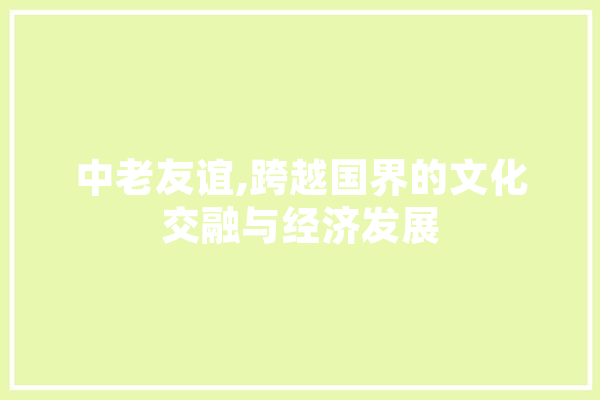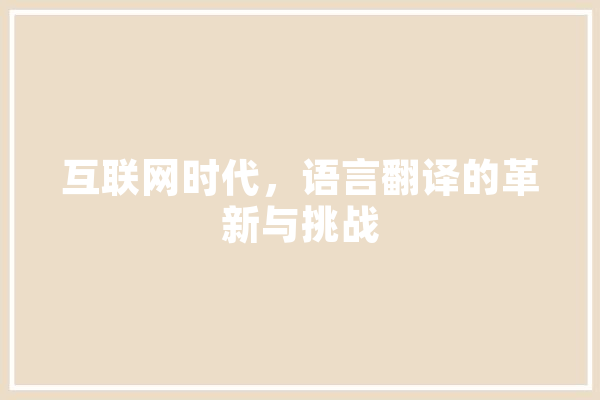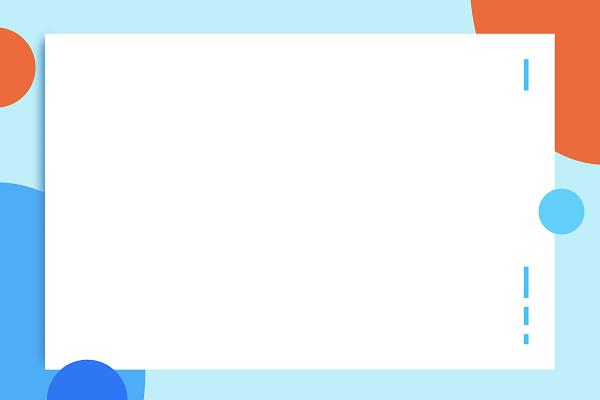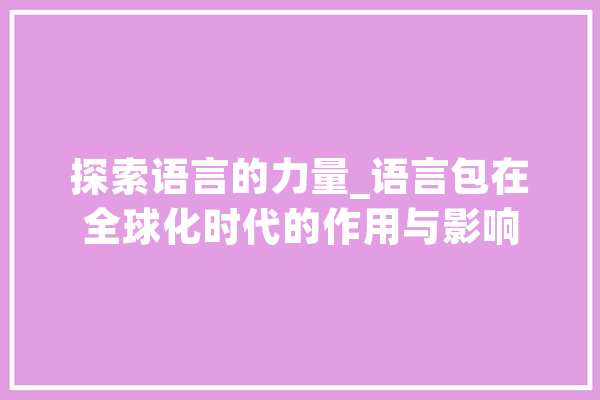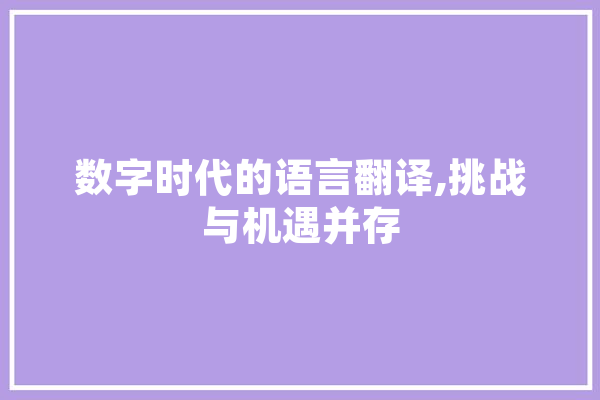南桥|对人工智能改进机械翻译的效果我持乐不雅观立场_机械翻译_措辞
1933年,亚美尼亚裔法国工程师乔治·阿特斯鲁尼(George Artsruni)得到了“机器大脑”的证书专利。这个机器大脑是用目标措辞中的单词,更换原始措辞中的单词,类似于今日Word的更换功能。这该当是机器翻译的较早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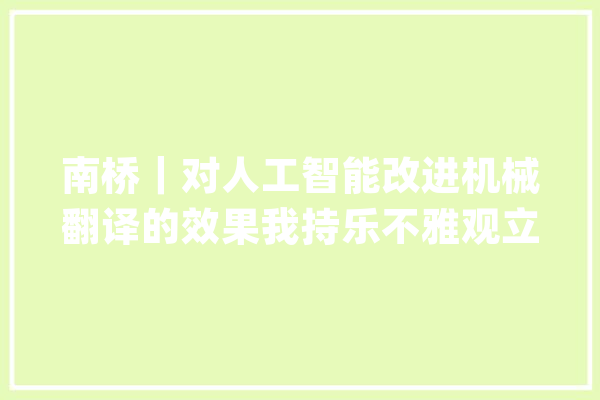
后来,机器翻译和打算机的发展并驾齐驱。冷战期间机器翻译达到了一个小高潮。美苏两大阵营,都存在大量译介对方情报之需。当时东西方互换少,翻译需求大,但人工昂贵。在1963-1965年间,美国政府花在翻译上的钱是1300万美元。翻译用度标准在千字9美元到66美元之间,比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的标准还赶过很多。1964年,美国成立了自动措辞处理咨询委员会(ALPAC),约请了来自贝尔实验室、兰德公司、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剖析机器翻译的未来,为美国国防部、中心情报局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等机构供应决策参考。
很永劫光以来,研究者对机器翻译还有一种思路,类似于柏拉图的现实乃理念之模拟一说:所有文本,如中文、英文,都是更为抽象的某个超级文本的解码。如果能回到这个抽象的超级文本上,再译成详细的措辞就不难了。这种理念化的文本,也反响人类对付思维逻辑性和规律的追寻。这一思路在理论上很美。有一种堪比巴别塔措辞的天下语在理论上也很美。但它们都忽略了人类措辞的繁芜、模糊、灵巧,和根植于详细环境的借景买卖。这些成分,造成了人和机器的关系千变万化。
现在的机器翻译核心处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不但是在找措辞规律,而也依赖日渐扩大的语料库。机器翻译可以利用统计学的规律,探求语料之间最为可能的对应。谷歌近些年提出了一个“神经机器翻译”(Neural Machine Translation)的说法,试图摆脱词汇、术语、句子之间的大略对应,而是试图在两种措辞之间,探求得当的对应,并实时纠正。机器自己在开展深度学习,不断纠正自己的缺点。这样一来,笔墨翻译的准确性会逐渐提高。对人工智能改进机器翻译的效果,我持乐不雅观态度。
在机器和人之间,最好的办法,是让机器做机器善于的事,让人做人善于的事情。人工智能对付翻译来说,是一种强大的赋能,而非狡诈的竞争。在文学翻译领域,受工匠思维的影响,作品被说成像机器翻译一度是见不得人的事。一句“机翻”的评论,能引发豆瓣上的一场一星运动的腥风血雨。好在此辩论也没空费,好歹让人们更为合理地考虑机器翻译的角色与定位。
在角色上,人类翻译能游走于上述繁芜、模糊、灵巧和情景之间,在理解的峰顶和夹缝之间,找到自己的活路。文学翻译不妨利用机器的力量,完成初始的翻译,然后再来动手,会节约大量人工。节约的韶光来自专业术语的统一,人名地名的翻译。中外文的对照翻译,放在同一个平台之下,也会使得重复性词语、术语翻译的修正更为简便。不然的话,两套文本在不同体系之下,查到原文的查不到译文,查到译文的查不到原文,无法逐一对应,无法一扫而空。
人和机器翻译谁优谁劣是个伪命题。机器不是有情绪的主体。机器没有和人类较劲的必要,人类也没有与机器较劲的必要。能利用机器翻译提高自己的效率和效果,才是明智的做法。那种阿尔法围棋和人类高手对决的场面,不应涌如今翻译领域。文无第一,译无第一, 只有不同的办法的失落手,和相得益彰的补充。对付人类翻译来说,机器翻译就好比苹果的Siri, 百度的“小度”,都是我们的人工助理而已。
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翻得若何”,而是“翻译什么”的问题。过去,翻译的文本,直接会影响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可以想象,如果《圣经》《成本论》《天演论》这些文本没有翻译,结果会是若何?
须要解释的是,不是所有的翻译都是有益的。在文学领域,美国翻译得很少,中国则为翻译第一大国,什么作品都翻译。已经公版的作品,由于无需支付版权转让费,一韶光百舸争流,多的乃至涌现几十种不同的译本。《瓦尔登湖》便是一例。比较不同的版本,都可以产生一门“瓦学”来,有这必要吗?真正主要的文献,尤其是对付我们对一个领域深入理解的学术文献,对付大众生活会有显著改进的文献,翻译又是匮乏的。
在文学界,中国出版界引进国外新书速率很快,新品泛滥。一有国外文学奖颁布,急速就被抢购一空。让翻译做完之后出版,没有一炮打响,也不想持续经营,赶紧去追下一本,把现有的书丧失落不管。这些做法,多属狗熊掰玉米,一起走一起丢。这种货大量足式的大批量引进,跟文学翻译太廉价,没多少本钱也有关系。指望译者用爱发电,做大他们的“码洋”,是荒诞的。缺少行业的组织折衷,译者最少可以给自己设个标准,把生存和生活的改进放在第一位,不要被各种情怀的说辞所误,只管即便少做一点。不过当我提出这个想法时,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但汉松教授的回应是:“不太可能的,往后译者议价能力会越来越低——由于一些高校正西席和研究生的译作开始计入科研分数或毕业揭橥(譬如两本译著折算为一篇c刊),只会有更多的人乐意成为廉价劳动力。”但教授说的是有道理的,把精良的翻译不当学术成果,是遗憾的。如果算成果,也要小心人类的指挥棒效应:你去衡量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当我们谈论翻译未来的时候,不妨考虑什么样的翻译,能够改进人本身的生活质量,而不是让人成为廉价劳动力。
机器翻译可以拓展我们的专业视野。在诸多小众领域,翻译的书或其他资料,可能看到人不多,出版社也不愿意做。外语水平欠佳的人又看不到,视野受到限定,不妨利用更多机器翻译,翻个大概:行家人有时候须要的精度也不是很高,如果机器翻译不断改进,准确性提高到八九十分,很多人工翻译是不须要的,凭借机器翻译即可。一些科技文献,业内人士借助机器粗翻的结果,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理解大体情形。一些仅需理解的解释笔墨,机翻完备够用。
机器翻译可以改进普通人的生活。保健、教诲、亲子关系、冲突处理、有效沟通等方面,有很多实用的资料,翻译出来会影响一个人人发展的轨迹,乃至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又有多少出版社在争先恐后去翻它们?如果能够借助机器翻译的力量翻译出来,也是大有功劳的事。在国际争霸期间,机器翻译是密查对方情报的手段。如今,我希望机器翻译成为改进人类生活的利器。
南桥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