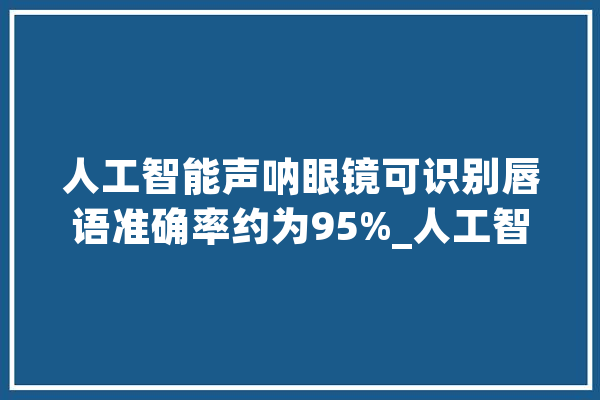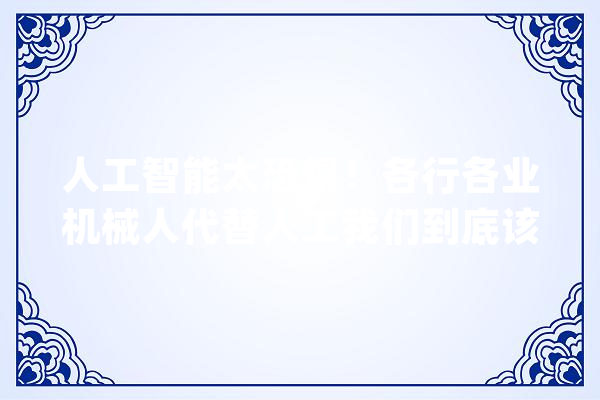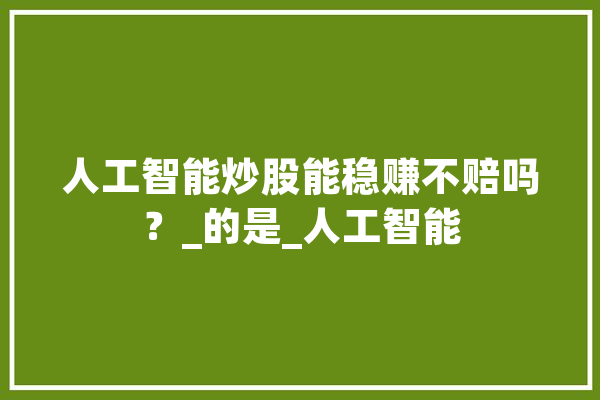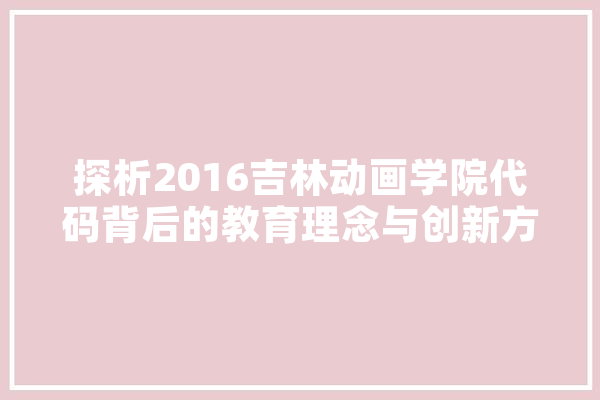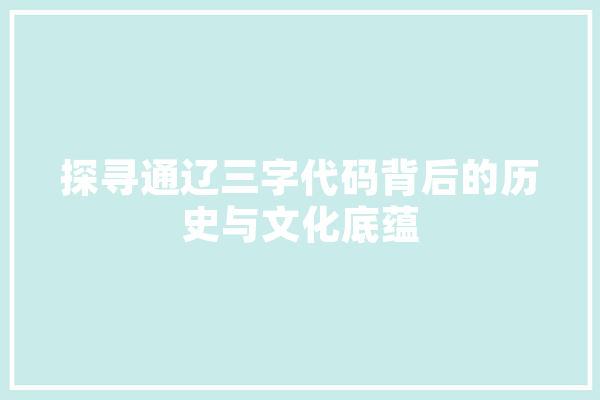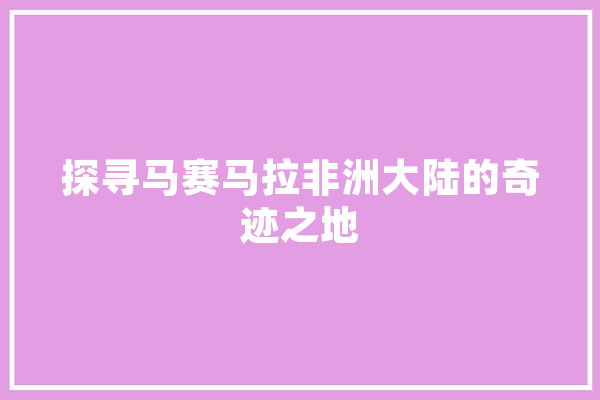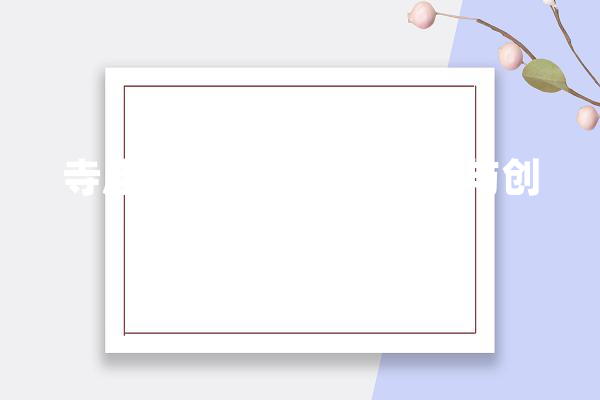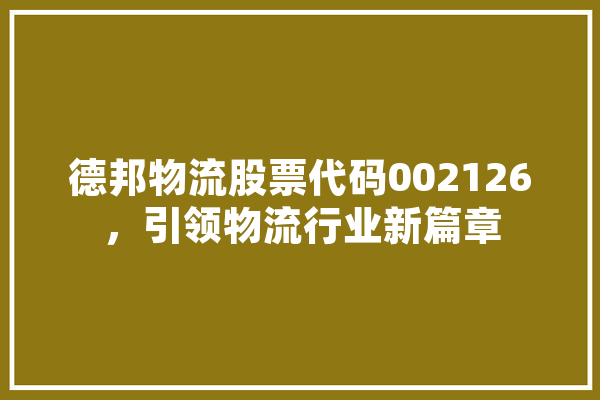智能制造时代是否还需要工匠精神?听听这三位“南京工匠”怎么说_工匠_工作
孙景南:智能制造时期更须要工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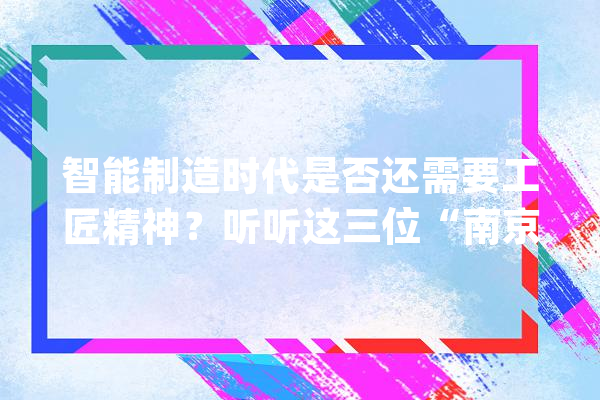
处理繁芜、创造性的事情
“南京工匠”孙景南是中车首席技能专家,她1990年进厂,如今已经在列车的焊接事情岗位上坚守了29个年头。 谈起“工匠精神”,孙景南有自己十分独到的体会:“就好比‘匠’这个字的写法——在自己本专业领域的框框里对自己琐屑较量,在事情细节上追求精益求精。”正是源自于对自己“不肯轻易放过”的哀求,孙景南在面对困难时总能彰显出一名“工匠”身上的执著。 在B型全焊接生产线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由于引进了全新的技能,产线上的焊接工艺总是会涌现不达标的情形。作为专家的孙景南自己一边做一边教,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换了各种操作手腕,可教出来的焊工徒弟干的活儿依然时常通不过考验。 “当时真的是反复地在磨。”孙景南回顾道,“我们先从小件开始,一次焊十副,每个人必须至少过六副;后来标准逐渐提升,在仿照事情实践中,每人在焊接边梁、整梁的时候合格率必须达到80%。末了到了产品焊接阶段,每个环节每人只许可有两次返工的机会。”在这种严苛的演习和磨砺之下,新建立的B型全焊接生产线终于将焊接事情的不合格率降了下来,正式投入到了生产当中。 “那段日子里,只要现场有生产,我们就得全程随着,常常一干就到半夜。”孙景南见告,“有一天晚上我刚放工回家洗完澡,结果第二天须要鉴定的首件产品创造了问题,返工了一次还是不合格,只剩下了末了一次重做的机会。于是我连忙又赶回岗位上,一贯忙到凌晨一点多才终极把问题办理。” 2018年,当这条产线上的标准动车组终于正式下线的时候,孙景南有了一种“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的感想熏染——“终于完成了我们这一代人努力了很多年的追求。”
随着智能制造时期的逐渐到来,车间也引入了许多自动化、智能化的前辈设备。譬如长达20余米的长直焊缝,如今已经可以通过机器手实现自动焊接了。但在孙景南看来,这正好对焊工提出了更高的哀求:“当这些重复的、呆板的任务由机器承担了往后,就更须要技能过硬的人来专门处理那些繁芜的、创造性的事情了。” 因此,在技能发展倒逼人力不断提高自我哀求的背景下,奋战在一线上的工人们就更加须要苦练内功。“生产制造越是智能化,就越是须要我们对事情有一种执著,越是须要像打磨艺术品一样去把每个环节做到最好、最俊秀。”孙景南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追求,同时也是每一位‘匠人’的初心。”
王强:智能制造对工人提出了新的哀求
依然须要敢于攻坚克难的钻劲儿
CRH6型列车车头虽然只有短短的4米,但却须要上百块铝板进行拼接组装。加之动车车头特有的流线造型,每台车头组装好之后都会有长达500多米的缝隙须要焊接。 “每条缝隙焊接之后都会产生一定的形变,因此焊缝多了之后就必须担保在前期组装时将车体构造的每个部件装置到最佳位置。”中车冷作钣金技能辅导王强见告,“装置高铁列车车头是一个须要不断调度的过程,对每一项工艺技能都有很高的哀求。” 高铁的每种新车型在最开始生产时都有所谓的“试制车”,许可试验和失落败,周期常日也会比较长。但中车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在制造CRH6型列车时,韶光进度非常紧张,于是公司决定把试制车直接作为成品,落地就要合格。 “第一辆车的装置每每非常繁芜,有太多的组件须要调度,为了试制这个车体公司专门把我调了过来。”王强回顾道,“当时从其他分公司请来的技能辅导全都认为不可能一次性搞出来,以是当时压力特殊大。” 随后,王强带领小组直接“住”进了车间,每天早起六七点就进场、一贯干到半夜才收工。“闭关”期间,王强和工友们对每一个部件、每一道工序都进行了多次校检,反复验证了很多工艺方法,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末了,当第一辆试制车终于搞出来的时候,我还是很自满的。”王强说,“这么繁芜的工艺,居然真的能一次性把它做好,不仅对全体车型的顺利下线非常关键,对我自己而言也是一次发展。”
身为“南京工匠”的王强见告,他对付工匠精神的理解,便是能够做到对自己所从事的行业百分之百的投入,碰着困难敢于寻衅,面对产品更是要做到极限。“在我看来,每次攻坚克难都是一个提高的过程。以是,面对寻衅一定不能投契取巧走弯路,而是必须铆足干劲、沿着直线一贯走。” 如今,车间的生产智能化、自动化水平越来越高了。不仅车底的装置设备全都换成了液压动力,同时产线上也配备上了翻转机,工人装置的时候再也不须要爬上爬下了,动动手指就可以将全体车体高下翻转、调度到得当的角度,很大程度降落了劳动强度。而最新引入的柔性化拼装设备乃至可以自由变形,赞助工人做的事情大大增多了。 “虽然智能化生产让工人们在体力方面轻松了很多,但在其他方面也会对人提出新的哀求。比方说自动扮装备故障了,同样还是须要精通技能的人去研究、去排查、去办理问题。”王强见告,“以是,工业生产智能化了往后一样还是须要我们干一行爱一行,还是须要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保持那种一股脑干到底的钻劲儿。”
屠跟林:智能制造尚未完备取代人工
不能放弃工匠精神
“南京工匠”屠跟林是中车工业涂装技能辅导,进厂36年来一贯坚守在生产一线,为列车的涂装事情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 2017年,铁路总局立项研究办理修理车外墙平整度的课题。“我们不仅要生产列车,还要修理。修理过后的列车外表得先刮腻子才能喷漆。”屠跟林见告,“腻子太薄,刮不平;腻子太厚,开裂和脱落的风险就会增大。以是我当时的任务便是确定修理车刮腻子的厚度保持在多少是最得当的。” 时限只有短短一个月,老厂区也没有什么专业的实验设备,屠跟林就用“土法”搞起了实验——为了仿照列车从广州到哈尔滨所经历的温差变革,屠跟林将样板带回了自己的家里,又是在烤箱里烤、又是在冰箱里冻。 “当时我太太都有见地了,她质问我说照这么搞,家里的东西还怎么吃。”屠跟林笑着讲道,“但是没办法呀,实验条件不足,我只能把事情往家里带了。而且我是专家,以是任务到了我这里就不能推。” 终极,屠跟林将修理车腻子的厚度区间锁定在3-5毫米之内,这样刮出来的腻子既不易脱落,又可以担保每米靠尺的不平整度不超过1毫米。随后,这一成果在中车集团内部进行了全体系推广。
目前,在轿车生产领域,涂装基本可以实现高度机器化与自动化。但在铁路列车制造领域,刮腻子和喷涂还是须要依赖手工。“虽然工业制造的智能化水平正在提高,但总还是有些事情须要人工来完成。”屠跟林讲道,“而且就算是生产制造高度智能化了往后,产品依旧是还是批量化的。如果想要打造佳构、寻衅极限,还是须要履历丰富、吃苦肯干的人来完成。以是我并不以为智能制造来了往后我们就可以放弃工匠精神了。” 作为这次采访的三位“南京工匠”当中工龄最长的一位,屠跟林表示自己今后依然会在一线岗位上一贯坚守下去。“所谓‘工匠’,首先是‘工’——我以为自己只有在实际生产的事情岗位上,才能发挥浸染、实现代价。”屠跟林见告,“以是我会在列车的涂装一线一贯干下去的。” 交汇点 陆威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