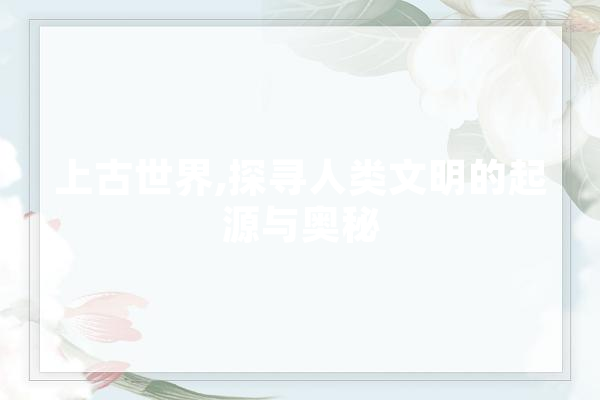人工智能无法周全取代人类_人类_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两个流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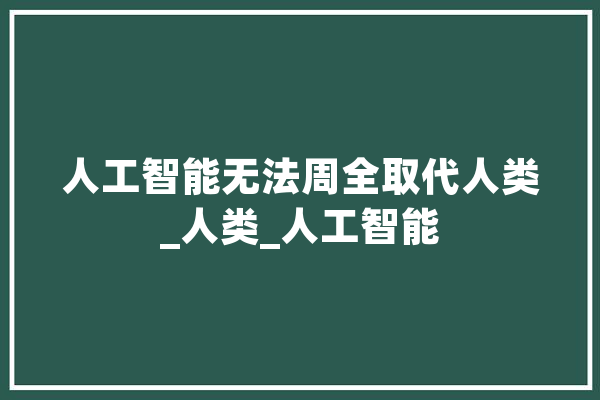
人工智能研究有两个最紧张的流派,一个是符号人工智能,一个是连接主义。前者的思路是固化人类在某个领域的一样平常知识,然后用逻辑学或者统计学的方法推理出其在特定条件下的分外形态;后者的思路是“喂”给系统大量的特定领域内的数据,然后在一个被数学化了的人工神经元网络模型中处理这些数据,终极使得该模型能够经由一定的“演习”而完成从特定类型的输入到特定类型的输出的映射关联。本日由于“阿尔法狗”而变得家喻户晓的“深度学习”技能,无非也便是结合了一定符号人工智能成分后的高等形态的连接主义技能。其在工程学方面的精妙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但其得以运作的基本科学框架,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早就已经被奠定了。
从利用角度看,符号人工智能最范例的利用模式便是“专家系统”,也便是仿照人类在某个领域的专家,就干系专业领域内涌现的问题进行自动诊断与应答。而连接主义或者深度学习的最范例利用模式则是“模式识别”,也便是对特定领域内的大量信息中蕴藏的固定“套路”进行以空想输出为标靶的识别。然而,二者各自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专家系统很难对超出编程者预见的崭新的专业问题进行有效应答,而连接主义也难以应对数据质量不高(或数量不足)、空想输出标靶不明的繁芜局势。更麻烦的是,二者目前都只能被利用于专业人工智能的领域,而无法做到“举一反三、交融贯通”。
机器全面取代人力仍在“科幻”层面
而下面的几个场景,就足以证明:没有这种“举一反三、交融贯通”的能力,机器全面取代人力的画面就将永久勾留在“科幻”的层面上。
场景一:自动驾驶。
自动驾驶目前已经成为人工智能投资的重点,有很多新技能已经被利用到自动驾驶的汽车上。比如,激光雷达、摄像头与高性能打算机的结合,能够使得车载智能系统准确地对车体自身的运动状态与干系周遭环境作出评估,而系统对付人类驾驶员履历的“移植”,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系统能够像人类一样对外界变革作出回应。
这些技能进步当然是故意义的。不过,说自动驾驶技能立时会全面取代人类驾驶员,则依然有言过实在之嫌:其一,自动驾驶系统的运作须要对海量环境信息进行搜集,而此类搜集活动在恶劣景象情形下会遭遇困难,与之比较,闇练的人类驾驶员纵然在这种情形下亦有“应变之道”;其二,海量环境信息的搜集未必会导向明智的决策,由于人类驾驶员在“紧急避险”局势下作出的直觉决策,每每因此忽略某些不主要的细节为条件的。而对付输入情报的“主要性”的高等判断,正好是眼前的打算机所不善于的;其三,人工智能对付个别老驾驶员履历的仿照,依然具有“知其然却不知其以是然”的色彩,无法根据环境作出有效的变通。举个例子说,一个适应了日本东京右驾驶座环境的老司机,只要经由适当的调度期,同样也能够适应上海左驾驶座环境,而一台仿照东京司机行为的人工智能系统,却很可能要经由彻底的重新演习才能够适应上海的驾驶环境。同时,不少中国城市普遍存在"大众年夜众交通法规意识淡漠的问题,也会为自动化驾驶技能的遍及预埋隐患。
场景二:工业化机器人。
在公众年夜众意识中,最能够与人类劳力构成竞争关系的,恐怕便是工业机器人了。但这里须要指出的是,工业化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本身并不是一个观点,由于前者的“智能”实在并不高。譬如,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所建立的特斯拉汽车的高自动化汽车装置线,虽然利用了大量的装置机器人,但是它们的运作完备以人类闇练工的“模板动作”为复制工具,无法像人类员工那样根据不同的车型作出变通。对付这样的机器人的利用虽然能够节省人力,但是其存在依然得预设人类劳动模板的存在,因此依然是寄托在皮上的毛而已。说这样的机器取代了人类,还不如说是人类自己的复制品取代了人类。笔者并不认为眼前工业机器人的进步具有实质上的历史创新意义。
场景三:机器翻译。
目前“科大讯飞”、“谷歌翻译”等软件在双语自动化翻译方面为民众供应的便利,当然是值得嘉许的,但认为这些产品不久后就会消灭人类译员,则显得过于乐不雅观了。
第一,人类译员的市场一样平常对应于高真个商贸活动与法律咨询活动,而这些活动所须要的翻译质量相对也比较高。比较之下,目前机器翻译最胜任的任务乃是大略旅游用外语翻译,与高端商贸与法律咨询活动并不构成竞争关系,因此也无法取代高端翻译人才。
第二,目前主流机器翻译系统的运行,都不得不大量“剥削”人类既有的翻译案例,而无法有效应比拟较小众的翻译需求——比如鄙谚翻译、小专业领域内的翻译,等等。“理解干系的文化与专业的背景知识”这一点却正好是眼前的机器翻译系统很难做到的。
场景四:家政做事员。
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趋严重,研发机器人家政做事员的必要性显然也就变得日益急迫起来。但眼前的“智能家居”研究依然离“取代人类家政做事员”这个目标非常迢遥。譬如,一个足够智能的家政做事系统应该能够听得懂人类的指令,而不须要人类对其进行再编程,这就预设了家政做事系统本身就已经具备了强大的自然措辞处理能力。但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眼前人工智能的自然措辞处理能力还是有点不尽如人意的。此外,一个足够智能的家政做事系统还应该有能力在彼此冲突的用户指令之间进行折衷——譬如既要“让房间显得井井有条”,又要“让关键性物品变得随意马虎被用户所获取”。这样高等的能力显然须要系统具备相称高的自主决策方案能力与目标设定能力,而这显然也超出了眼前人工智能技能的发展现实。
场景五:机器人秘书。
机器人秘书也便是能够为用户供应文案事情助理的人工智能系统。只管此类人工智能系统在机票预订、固定模板文案天生等比较大略的专业领域内,的确能够部分取代人类的事情,但是其灵巧性却是远输给人类的。譬如,如果一个人类用户是一个物理学家,并命令机器人秘书去过滤掉“所有民科分子写来的电子邮件”的话,那么,系统又将根据什么标准去将“民科”提出的科学问题差异于专业的科学家提出的问题呢?这就将倒逼这样的人工秘书系统预装一定的专业知识。但眼前的人工秘书系统却又普遍不具备在赞助文案事情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跨领域推理能力。换言之,更为繁芜的秘书事情,还须要依赖人力资源。
综合以上谈论,我们不丢脸出,在自动化驾驶、工业化机器人、机器翻译、家政做事、机器文秘等领域,眼前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全面取代人类的前景还不明朗。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