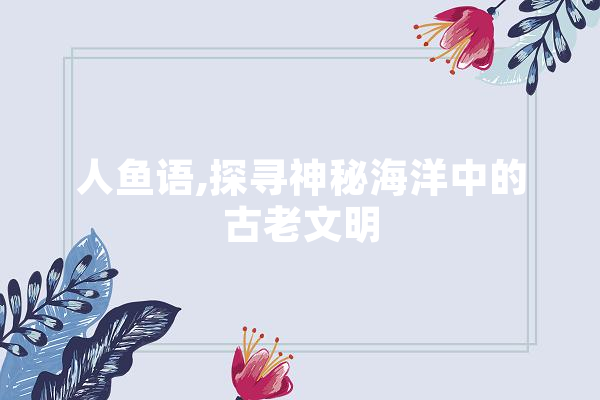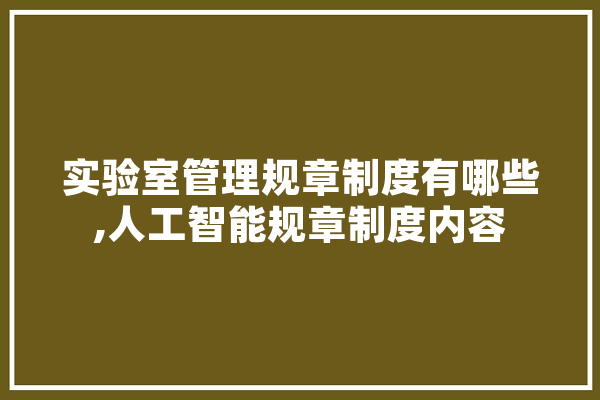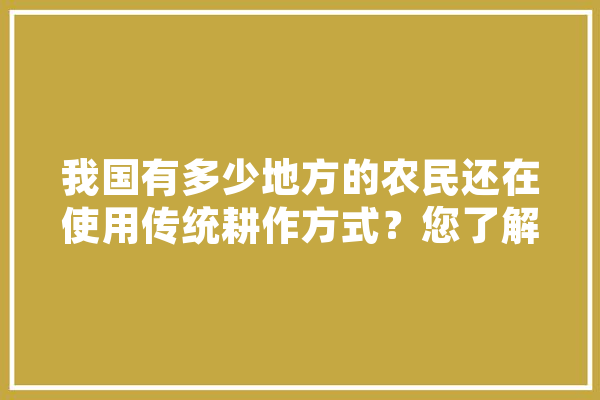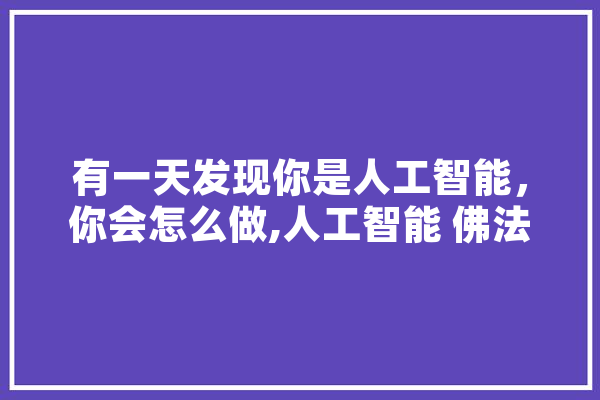深度!“文明对话”中的几个关键词_世界_中心
文明因互换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印证,也是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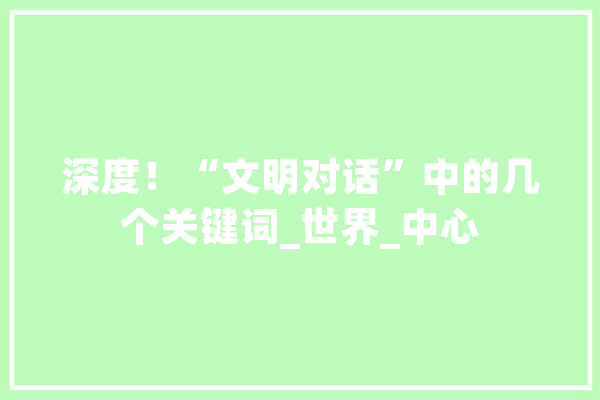
文明不是独大,更不能霸凌;而是平等、尊重、互助、对话、互换、学习和采借。随着环球化的到来,“文明对话”在新的语境中有了全新的含义。
那么,如何准确理解新语境中的“文明对话”?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导彭兆荣为我们总结出五大关键词,一起来看!
中西方的“文明”观点原来不一样。我国“文明”一词初见于《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经学家孔颖达释:“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又疏:“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中华文明的核心代价可精简为:天地人和、农耕文明、万物荣华。“中”乃天地之中也;“华”,《说文》:“华,荣也”;繁荣昌盛也。
西方“文明”,指人类所取得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状态与条件。其核心代价可精简为:以人为本、海洋文明、公民社会。“文明”仿佛筷子与刀叉,不能用“进步/掉队”“文明/野蛮”比较较,而该当以尊重、原谅、借鉴的态度待之。因此文明对话、文明互换、文明采借尤显必要和主要。
1 | “人”与“仁”的对话
天下不同的文明差异甚殊。以中西方文明为例,美籍华裔人类学家张光直在比较中西方文明时,利用“连续/分裂”的观点,即中华文明是“连续性”形态,而将西方的文明叫做“分裂性”形态。他认为:“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天下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革法则。因此,在建立全天下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利用西方的历史履历,也尤其要利用中国的历史履历。”美籍华裔学者、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维明将中华文明“存在的连续”概之为三个基本主题:连续性、整体性和动力性。
“文明对话”,“人”是主体;人是文化的携带者。天下上不同的文明体系授予“人”不同的涵义,也授予文明类型的差异。西方文化以“人”为主干建构出干系的语义群:人类、人性、人性主义、人本主义等,词根为拉丁文的“humanus”,核心代价是“人本”。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有一句名言:“人为万事的尺度。”概而言之,西方的“人”突出“我”(个体性)。
西方学者对人本主义基本特色总结如下:以人的履历为核心和主体;在此根本上所形成的知识系统编制;物质天下的关联与人类的认知形成了相互连接;人类生活和代价具有主要性和肃静;人类的认知和知识在现实中具有办理实践问题的能力;人类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变革中保持与真实性互证;个体身体(身心)是实践和实现道德的主体;人类具有反思能力和乐不雅观态度;历史上的“英雄”对人们具有不同方面的榜样代价;人的思想解放和自由表达具有至关主要的意义。以上不雅观之,所有的这些特点皆以“我”为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和”的宇宙不雅观,农耕文明中景象(节气)与物候的纽带关系,以宗族为根据的扩展线索,以及“家国天下”抱负等,反响在“人”的代价中,“仁”为紧张。仁,即二人等同、相敬,表示大家相等,同情原谅。“仁”的本义为尊重人性,相信人性相通,视人若已,同情宽待,尤指强势者对弱势者的宽容、厚道。《说文解字》有云:“仁,亲也。从人,从二。”《礼记·经解》:“高下相亲谓之仁。”概而言之,中华文明中的“人”强调“我”(群体性)。
由中华文明的“人不雅观”天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历史逻辑,亦可治疗以唯我独尊(如“美国优先”)盛行当下的“天下病症”。
2 | 两个中央:各美其美
“中央”的认知是一个有限合理的悖论。从认识论的角度,人们认识天下因此“己”为中央向外推展的“差序格局”,即像石子一样平常投入水中,一圈一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薄,人的社会关系格局因此建立。由此推演出“我群—我族”“近我/远我”的关系格局。比如,在以“欧洲中央”(“罗马中央”)的格局中,中国被置于“远东”;而在我国传统的“一点四方”的认识论中,中国是天下的“中央”。天下其他古代文来岁夜都有自己的“中央说”,险些没有例外,比如古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等。“中央”认知性直接证据:天下各国的舆图常日将“本国”放在中央位置。
在古希腊,“天下中央”有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天神在浑沌中创世,却无秩序,亦无中央。为确定“天下的中央”,天神派两位天使向两极相反的方向翱翔探求,末了在希腊的德尔菲会合,那个会合点即是“天下的中央”——天下的立基之点。古希腊的原始城邦大都有一个至高点,也便是所谓的“中央”,它因此城市为根本建立的国家政治系统编制。现存的雅典卫城遗址“Acropolis”不失落为西方古代国家形态的典范模型。“Acro”意为“高点”,延伸为崇高、权力等意义。“polis”为城市国家,与“政治”(politics)同源。这种权力关系需展现和展示在“公共场域”(public field)。“共和”(re-public)的原始意思指的正是在公共场所中的“公道”“公开”“公正”特性,强调“公民”“"大众年夜众”“公权”。“Public”是谈论大家共同关心事务的场所。这种文明系统编制为“欧洲中央论”奠定了根本,被阐释者有目的地建构为“天下体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了“文明冲突论”的隐线和隐患。
中国有自己的“天下体系”,中华文明的政治地理学也秉承“中央”(包括“中国”)理念,这便是“一点四方”的形制。依据学者的剖析,“天下”这一核心观点包括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天下全体大地。在存在论语境中大致为中华文明之立基构造“天、地、人”中的“地”。地为天下之“大家”所共有,是最大的公物和财产;
第二层意思:天下上的全体公民。在政治社会语境中相称于“民”。更准确地说,是指所有人的民气所向,即民心。故,得民心者得天下;
第三层意思:一种天下制度。在世界管理的办法方面,天下制度便是天下的存在形式,“家、国、天下”贯穿着家庭性原则而形成三位一体的构造,即从“家(个人)”—“国(大家)”—“天下(全人类)”。
从人类认知角度看,以“我”为中央是认知的主要办法;从政治地理学角度看,不同的群体因此形成了“远近关系”,进而形成权力关系。以是,任何“中央论”都是认知性的,是有限的。因而都要本着“各美其美”的原则,不可因此而“霸道”、“霸权”和“霸凌”。比较较而言,“天下体系”较之“天下体系”更具备平衡力,更符合天下“道理”。
3 | “三元法则”与“二元对峙律”互鉴
中华文明的核心代价是“天人合一”。“天地人和”为“三元”布局,相互协作是中华文明的认知性法理。这种“天地人”的通融并非静止,而是动态,形成所谓“回”的周转。《说文》释:“回,转也。”它以天地日月为参照;“易”(日月)变革旋转而为永恒。这种代价不雅观还与生命律动相合营,与农业伦理相结合,即所谓“天时”与“物候”相谐。《吕氏春秋·诬徒篇》有“世,時也”,也是中国农正(政)之农业伦理中最契合的“生命”(时)的表达。
值得一说的是,“天地人”之三元表示在“三(参)”中。“参”本义指父老仰不雅观天星,参辨方位。《说文解字》释:“参,曑和商,都是星名。”我国古代天文学及民间对“参宿”指猎户座(ζ、ε、δ)三颗星。“三星”有“天作之合”的美意。由此可知,中华文明之文法所遵照的为“三元法则”。
西方文明中的“二元对峙律”不仅为认知事理,且为实践原则。法国人谢和耐认为,“同中国或印度思想家适成对照的是,在希腊哲学家的智能领域中,存在着一种对实在与天生、观点与觉得间的截然两分法。它不纯挚是在修辞学的对语间确定一系列对立关系。这些对照的观点,被分成两两一对,汇而形成一个完全地界定两个相互排斥的领域的二律背反系统。”“二元对峙律”之于认知事理有其称道之处,比如,西方自然科学领域的真理与谬误、对与错等,科学家对事物的认知也只能在对与错中选择,却无对与错并存的真理。然而,将“二元对峙律”用于不同的文明、文化、社会和族群便可能出问题,那种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白即黑的大略、绝然之法则正是导致当来世界纷乱的一个缘故原由。
中国传统的文化要义中并非没有“二元”,比如阴阳。《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革,一上一下,合而成章。”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二元”是构造要素,而非对峙关系原则;“阴阳”成为同构性的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4 | “四面八方”:唯我中华
西方的文明,若以拉丁系溯源,属于“海洋文明”类型,其特色包括拓殖、争霸、冒险、尚武、战役、光彩等,也随意马虎滋长天下霸权思维。凡举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航海、库克船长南太平洋探险、欧洲移民的“五月花号”、“三角贸易”等无不与之有关。
中国素以农耕文明而著称,其特色之一在于“和”(和气、和土、和谐),并在此根本上形成以“四面八方”为关照的基型。中原共主黄帝的形象为“四面”。《太平御览》卷七九所引战国时佚书《尸子》中一段“论语式”对话:
子贡曰:“古者黄帝四面,信乎?”
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计而耦,不约而成,此之谓四面。”
“黄帝四面”符合中国传统的“天下”之“四海”“四方”“四象”“四季”之四方不雅观照,也是“中”与“四方”的关系写照。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战国佚书四种,个中《十六经·立命》篇记载“黄帝四面”之神奇样子容貌:
昔者黄宗质始好信,作自为象,方四面,传齐心专心。四傳自中,前参后参。左参右参,践立履参,因此能为天下宗。
“黄帝四面”与其说是神话,勿宁说是农耕文明之“天下不雅观”,这在《山海经》中有完全的描述:即以山为经,以海为纬,“山海”为“天下”之衍义,造就了一个“东西南北中”的建制。中(中华、中国、中原、中州、中心)皆由此而出,原型正是一点四方。
至为主要的是,“中”者,致中,致和也。《说文》释:“中,和也。”何以“中”释为“和”,《说文》曰:“和,相应也。”《广雅》:“和,谐也。”因此,“中”者,通天地之和,告天地之事。“中和”乃中华文明之紧张。
5 | “丝绸之路”“五互”:互尊、互信、互惠、互补、互动
“丝绸之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天下遗产分类中属“线路遗产”。2014年,我国的“丝绸之路”得到线路遗产名录,并成为同时拥有现存天下上最长人工运河与天下最长遗产线路的国家,可谓实至名归。
“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相契合大致有以下诸点:
万物之“理”取之于“道”。“线路”即“道路”。《说文》:“路,道也。”“理(道理)”文明和哲学的渊薮,且与“德(道德)”同构,而以“道”为名的哲学惟中国之道家。中国自古有“天道—人性”之说,以“天道”命“人性”一贯为政治地理学上的依据。历史上的行政区划,“道”“路”也成为史上区域管理的一种制度。逻辑依据为:以“道(伦理教养)”管理“道(行政单位)”。
“文化线路”这一历史征象受到当代人类学研究的特殊关注,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德著作的《线路:20世纪晚期的旅行与移动》,以历史上的线路为切入点,谈论人类通过线路所建立、建构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空间置换实践”。换言之,“线路”成为文明和文化的紧张构建办法。本日的“环球化”授予了这一“线路语境”新的属性,即“移动性”,包括人的移动、文化的移动、科技的移动、信息的移动、财物的移动等。在这种情形下,任何形式的“封闭”也越来越困难,“开放”是大势所趋。
“一带一起”培植无论是承接历史“丝绸之路”之遗产,面对当世混乱之形势,还是泰然应对诸多寻衅,都旨在凸显和强调“五互原则”:互尊、互信、互补、互惠、互动,即平等相待、诚信友善、上风互补、互惠共赢和共同发展。
人类的进步是建立在文明互换、尊重、平等、原谅、互利的根本上,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基石。如果文明是建立在不平等、不尊重、恃强凌弱、唯我独大的根本上,天下便永无宁日。当“美国优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同置于文明之天平,孰轻孰重,孰优孰劣,孰是孰非,人类自有公认,天下自有公断。
选自 | 公民论坛杂志7月下
转载请注明来源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