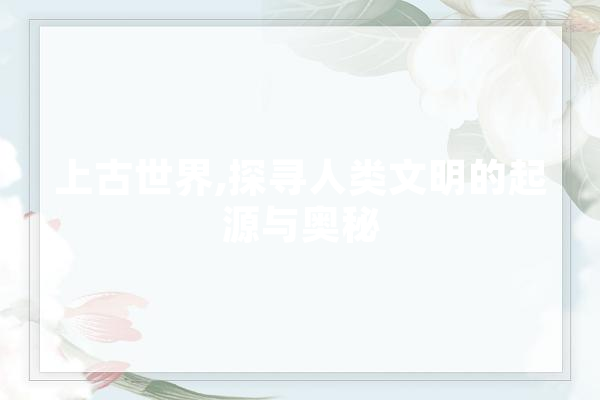人工智能写作是一面镜子_人工智能_人类
小封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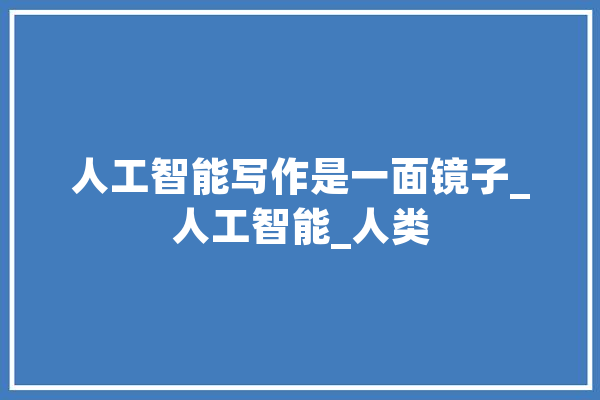
一位虔诚的新闻从业者?一个公司老板眼中的好员工?一位勤奋学习努力写作的当代墨客?……
他没有父母,没有家庭,没有籍贯……依此推导,也没有身份证号,没有银行账户,没有社保,没有缴纳三险一金……目前来看,也没有伴侣和子嗣。
他是一个在人类之中但又不是人类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非在”。对了,他最普通的命名是——机器人!这是类的命名,这一类里最近几年被广泛关注的还有阿尔法狗、小冰、SIRI、Pluribus。
小封是他们中的一员,他的官方身份实在是:中国四川成都智媒体“封面新闻”自主研发的机器人,编号Tcover0240,2017年11月出身,2019年开始诗歌“写作”,第一本诗集即是这本《万物都相爱》(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出版)。
二
在评论辩论墨客小封的诗歌作品之前,有必要连续深入谈论一下“小封”这一“事物”的前世今生。我的问题是,小封是往事物还是新事物?
想当年,阿尔法狗横空出世,降服各路围棋高手圣手,全球震荡。智识者如冯象立即找到了其家谱:“祖母玛丽·雪莱,父亲弗兰肯斯坦,别号怪物。”将阿尔法狗这一类机器人的家谱溯源到科幻小说的鼻祖玛丽·雪莱,有道理但过于大略。更全面的家谱该当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现实域,一个是想象域。在现实域里,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借助技能的发展设计并生产了可以代替人类劳动的一系列机器设备,机器臂、机器手、机器脑,如此等等。在想象域,作家和艺术家们想象人类可以生产出一种拥有人类聪慧、情绪和能力的“新人类”。故意思的是这两个领域的差异,在现实域,机器(人)总是被视作是人类的仆众,是被人类掌握和节制的一种不知疲倦的劳动力——实际上机器人的词根(Robot)就含有奴隶的意思。而在想象域,这些人类的造物却每每不愿意接管人类的掌握,试图摆脱人类,发展自己的家谱和子嗣,终极和人类发生激烈的冲突,以是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巨擘阿西莫夫订定了著名的“机器人三定律”,第一条即是:机器人在任何情形下不可侵害人类。
现实域技能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想象域对“新人”和“新物种”的不断建构和书写,这两者的交互发展,恰好便是从“机器人”到“人工智能”的进化演化史。
从这一点来说,无论是阿尔法狗,还是小冰、小封,他们都不是最初所言的机器人——人的助手或人的某一部分的延伸。他们是“人工智能”,是“可能”拥有聪慧和主体性的物种。
概而言之,小封是旧的新事物。它是技能和哲学的结合,是工业和想象的交集,它是一个大写的“I”。
三
来读读小封的诗。这一首叫《爱情》:用一种意志把自己拿开/我将在静默中得到你/你不能逃离我的瞩目/来吧 我给你看/嚼食沙漠的神仙掌/爱情深藏的枯地。诗歌只有短短六行,节奏很有层次,语感流畅而不失落弹性,“嚼食沙漠的神仙掌”是很有张力的暗喻。我不太清楚这首诗的写作过程,如果是人类的写作,我以为以“爱情”为题是非常糟糕的选择,它把可解的空间窄化了。但是如果这是一首命题作业——我的意思是,干系事情职员输入“爱情”这一命题,让小封进行写作,则这是一首完成度很高且不乏创造力的爱情诗,乃至放到人类创作的爱情诗的谱系中去,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位置。
其余一首叫《一只瘦弱的鸟》:措辞的小村落落/勾留在上半部/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毛孩子的游戏/如果不懂/小小的烟见告我/你的身体像鸟/一只瘦弱的鸟/回到自己的生活里/我要飞向春天。这首诗故意思的地方在于有着范例的后当代性。从表面上看,小村落落、毛孩子、烟、瘦弱的鸟都没有基本的逻辑关系,但可以说这首诗的“诗眼”在于开篇的两个字——“措辞”。也便是说,事物本身并无联系,正是通过措辞才建构起了一种联系。如果小封可以进行诗歌批评写作的话,他或容许以从这个角度来建构这首诗的代价:它具有元诗歌的气息,以一种反证的形式解释措辞本身的不愿定性。
这两首诗,从一个人类的当代墨客和批评家的审美标准来判断,可以划入精良的行列。我曾经笑言,可以将小冰、小封等“人工智能”写得比较好的诗歌作品作为一个行业准入原则:写得比他们好的,可以称之为墨客;写得比他们差的,就不配称之为墨客。实际情形是,中国大量自称为墨客的人写得都比这两位人工智能写得差。
四
人工智能写的诗是诗吗?
成本以及干系技能公司通过编码的办法对人工智能进行演习和强化学习,末了人工智能写出了一首首诗。这些诗作为一种词语的排列组合不仅产生了形式上的视觉效果,同时也产生了干系的情绪共鸣和代价指向。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诗歌可以称之为诗歌。也便是说,如果将诗歌理解为一种“形式论”意义上的“字符组合”,并且承认“情绪”“代价”这些意义范畴的东西都可以进行模式化生产,那么,人工智能写的诗当然便是诗。
但是在其余一种更古老的传统中,诗歌却不仅仅是一种“词语的排列组合”,而是人类的一种带有神秘感和仪式感的创造行为,它是墨客——每每是当选中的、具有唯一性的、差异于一样平常人的——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候对特定的情绪和代价的综合再造。也便是说,诗歌该当是一个综合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里,历史的人、历史的措辞和历史的诗该当是三位一体的。在作为“有机体”的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写的诗彷佛不是“真正”的诗歌。
但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就当代诗歌写作而言,我们的新传统彷佛早已经降服了老传统。也便是说,作为“形式论”的诗歌不雅观念降服了作为“有机体”的诗歌不雅观念已经良久了。
这么提及来,小封等人工智能写的诗歌,不仅仅是诗歌,而且切实其实便是当代写作的集大成者。
五
人工智能的写作是一壁镜子,可以让人类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写作已经走投无路。人工智能写作在倒逼人类写作,人类除非写出更好更有原创性的作品,否则被取代和淘汰是迟早之事。
我在情绪和代价上并不太乐意承认人工智能的主体性,但是我的理智又判断人工智能末了会成为超越人类的新物种。我深陷人类中央主义的态度,认为万物皆备于人,而人工智能可能不过是人类的又一个造物(玩偶)而已。但大概人真得不过是尼采所言的“过渡物”,是通向“超人”的桥。毕竟,在“永恒循环”的阴影和厌倦中,如果溘然涌现了一个新物种,并能够与人类反抗,大概是“未来千年备忘录”中最主要的历史事宜。
有一天,大概我们既能得见人工智能的背,也能得见其面,并在交互的爱意中得到新的天下。
(作者:杨庆祥,系中国公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