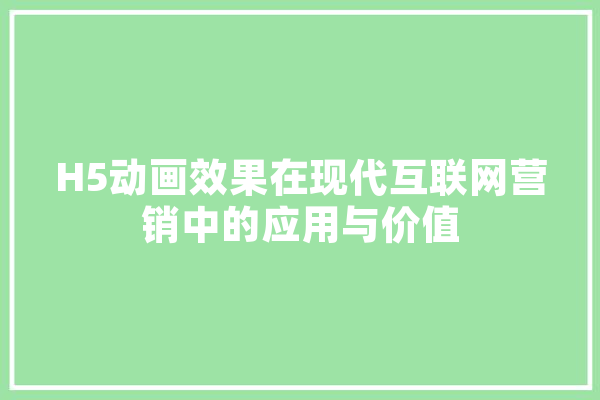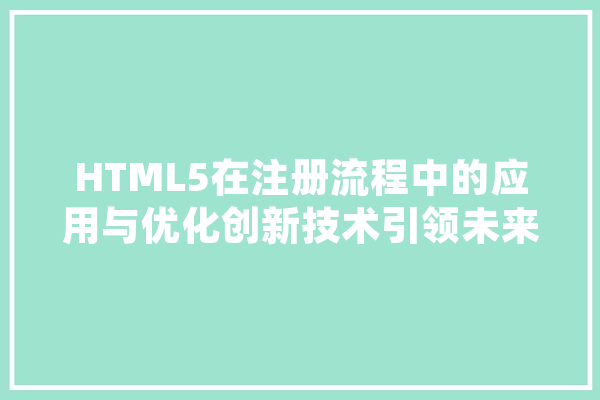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核阅_人工智能_意识形态
当今社会,以大模型、天生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正在环球范围内发达兴起,掀起了新一轮数字智能化浪潮。人工智能具有渗透面广、更新速率快、带动性强、影响深刻等特点,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家当变革的主要驱动力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引擎。但人工智能具有“双刃剑”效应,裹挟了许多具有新特点的意识形态风险,必须“主动识变应变求变,主动戒备化解风险”,促进人工智能“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领悟,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康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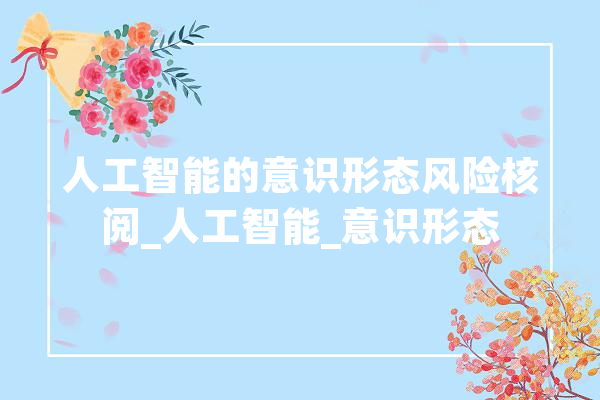
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表达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前沿科学技能,承载着生产力功能。它的强大功能使人类对其依赖进一步加深,存在着异化为一种影响人、掌握人、操纵人的无形力量的可能,被授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西方国家作为人工智能领先的市场化主体,节制着人工智能的内容政策和算法规则,使人工智能具有成本主义政治方向和代价取向,能够通过干系数据天生定制化的内容和信息,向受众贯注灌注“西方中央论”的意识形态,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管西方代价不雅观念,在代价塑造上表现出光鲜的政治方向。西方国家的人工智能存在数据霸权属性,紧张表示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工智能的数据剖析是建立在现有数据根本之上的,西方国家通过“云法案”,赋权政府掌控本国企业在境外采集和存储的数据,借此对他国数据实施“长臂统领”,仅许可“一家独大”,企图支配、操控他国数据。另一方面,科技环球化背景下,西方国家凭借科学技能主导地位实行科技霸权主义,借助技能手段为意识形态渗透和扩展供应便利,拉大了发达国家和掉队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将现实领域的霸权延伸到数字空间。在进行对外交流时,随意马虎涌现技能强国制约技能弱国的征象,呈现出明显的科技政治化方向。
人工智能的文化软实力属性。西方国家的人工智能文化软实力属性紧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的人工智能算法天生内容掩饰笼罩了深层的文化霸权,从客不雅观上起着粉饰西方国家霸权行为的浸染。当这一技能被不良利用或滥用时,会催生出大量虚假信息,扰乱大众视线,降落大众的信息判断力。二是西方国家人工智能的算法模型蕴含了天然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偏见,它的政治态度、代价取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是根本对立的。
如今,随着技能进步,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较高,能够根据利用者的输入习气,推算出其政治不雅观点、代价取向及行为特色,进而剖析、勾引利用者的代价取向。
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表征
人工智能技能以更加隐秘的办法表示国家意志力,成为再现国家权力的技能“镜像”,对现实天下具有反浸染,对主流意识形态带来新的寻衅。
人工智能诱发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弱化风险。人工智能技能运行机制深蕴成本逻辑,在成本的操纵下,人工智能通过设定与成本逻辑相符合的算法规则、代价判断,对用户进行特定“信息投喂”,大量主流意识形态信息在成本逻辑的“挑拣”中被暗藏,不断解构社会个体已形成的认知和代价。加之人工智能存在算法黑箱、数据偏见等弊病,只天生内容,无法辨别内容本身的真假,而虚假信息每每由于博人眼球、迎合用户被推送至信息前沿,使信息场域真假难辨,进而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难度加大。此外,人工智能措辞模型天生的话语信息具有拟人化风格,大量缺点思潮在人机对话过程中得到广泛而隐秘的传播和渗透。人们在拟人化风格的“迷惑”下,极随意马虎陷入西方的“话语陷阱”,使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引领力面临弱化风险。
人工智能诱发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话语消解风险。人工智能的话语生产是一种“从有到有”的生产过程,缺少创造性和批驳性,并未充分发挥“现实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创造出富有想象力和创新性的内容。同时,人工智能具有个性话语生产、多元话语选择、精准信息推举等功能,致使大量所谓多元化、意见意义性的话语冲击了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的逻辑性、政治性强的威信话语,对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话语的传播力、勾引力、公信力造成极大冲击。
人工智能诱发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传播失落范风险。人工智能受成本逻辑和算法逻辑的操控,随意马虎使人们陷入对人工智能的依赖,造成“信息茧房”。当人们长期禁锢在“信息茧房”中,会固化人的思维和意识,加剧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和代价偏见,使人异化成“单向度的人”。在“信息茧房”浸染下,人们会依照个人的喜好选择和过滤信息,只对自己偏好的信息感兴趣,排斥自己不感兴趣的信息,使各种不良社会思潮以更加隐匿、繁芜的办法传播,对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产生强烈的冲击。
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的规避
人工智能技能所诱发的意识形态风险已经成为掩护国家安全、政治安全不可回避的新课题。因此,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戒备,掩护公民利益和国家安全。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辅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辅导思想,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和行动指南,才能培植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规避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风险,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辅导地位,增强马克思主义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话语权和主导权。
要光鲜地反对和批驳缺点思想,利用马克思主义阐发人工智能蕴含的成本逻辑和算法逻辑,揭开人工智能的“神秘面纱”。通过将马克思主义话语置于人工智能话语体系之中,创新马克思主义话语表达,使人们在打仗人工智能时不自觉地打仗马克思主义话语,减少马克思主义与"大众年夜众的间隔感,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影响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话语权。要站稳中国态度,讲好中国故事,做到因时而动、因势而新。通过挖掘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故事以及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上风的故事,剖析比较“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同,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胜性,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能与中国本土5G技能、区块链技能等相结合,传播中国声音,使中国故事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
第二,筑牢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的引领浸染。面对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我们要捉住机遇、实现新打破,以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引领网络社会思潮。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在人工智能技能发展中的代价不雅观导向浸染,提高"大众年夜众的理性判断力,戒备化解意识形态风险。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通过把社会主义核心代价不雅观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植入干系数据库,确保人工智能产出的内容彰显党的意志和主见。
要努力打造一支政治性强、本领过硬的意识形态事情军队,充分发挥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头羊”浸染。要结合网络热点难点,提高干系职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时,干系职员要充分发挥主不雅观能动性,加强对人工智能前沿理论和技能的学习,成为信息生产、传播和吸收的“把关人”,积极参与网络舆论勾引,提高意识形态事情水平。
第三,要依法依规加强网络空间管理,推动人工智能法治化和道德化发展。面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意识形态风险,要坚持底线思维,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技能开拓和运用的法律制度及伦理规范,掩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要加强人工智能的立法事情,健全、完善人工智能风险戒备、管理专门法规,推动干系法规落实到位,形成以“硬法”为主、“软法”为辅,“软”“硬”结合的人工智能意识形态风险监管机制,推进网络空间法治化进程。
人工智能的目的在于知足人的生产生活需求,是一种技能性工具。但是,如果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它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掌握”和“驾驭”人的思想行为,使“物”挟持了“人”。因此,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不雅观念,绝不能让技能凌驾于伦理之上,要以“现实的人”为尺度,提高个体的数字素养和技能,使个体故意识、有能力应对个中存在的代价偏见和风险,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地做事于社会进步。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