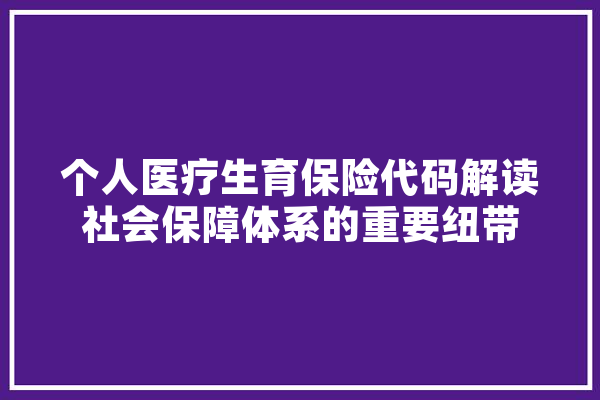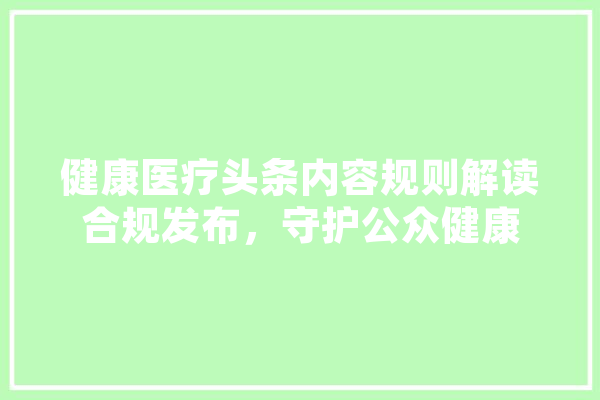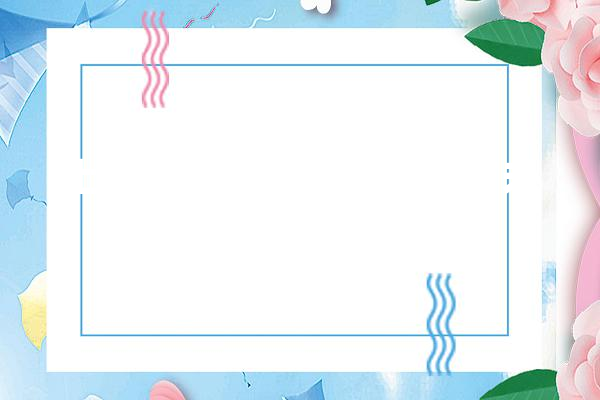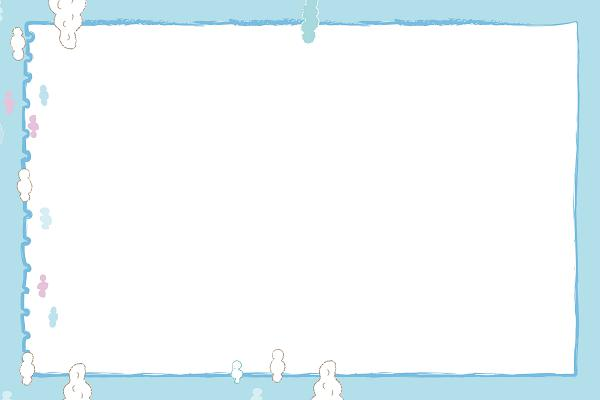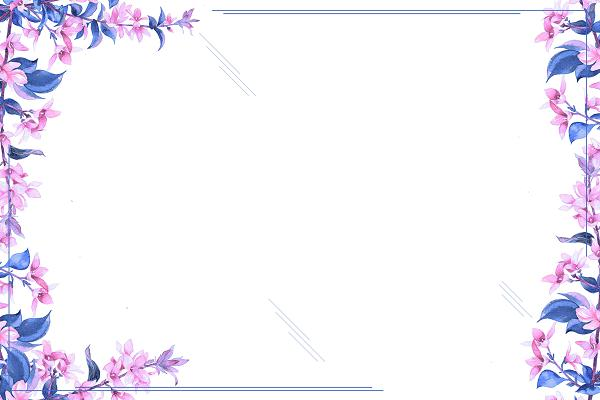医疗器械+人工智能新风口来了?_医疗_上海
◆火神山医院正在安装AI医疗设备。深睿医疗供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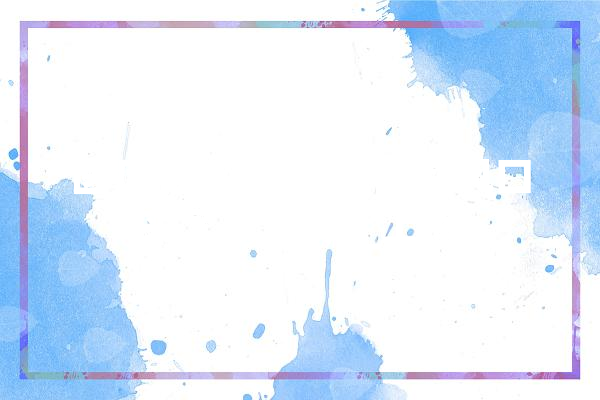
新冠肺炎疫情让环球一度涌现一罩难求、一机难求的局势。一罩指口罩,一机指呼吸机。医疗东西由此成为关注热点。
在医疗东西领域,我们的技能水平长期以来并不占上风,并且高度依赖入口。但如今,在人工智能运用上,经历了疫情的“大练兵”后,智能影像诊断、远程医疗等,让中国积累了更多自己独占的履历。
未来,医疗东西+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某种弯道超车的可能性?而上海在迈向科创中央的过程中,又能在这个潜力无限的创新领域捉住哪些机会?
多年差距困难追赶
近几个月,吴东博士不断收到来自宁波、深圳等城市的邀约,希望她能带着新组建的医疗东西团队,入驻当地。但吴东暂时还在考虑中,上海的研发人才和技能积累,相对更有上风。
对上海的好感,缘起于2011年。那时,中国医疗东西水平发展严重不敷,环球500强巨子企业不愿意错过弘大的中国市场,纷纭操持着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央。吴东曾任3M、柯惠的高管,2011年起供职于美敦力,她为公司的研发中央选址,当时有4座候选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天津,而她终极选择了上海。
10年过去了,但是吴东创造,海内的医疗东西公司,依然与国际上有很大差距。
以呼吸机为例。呼吸机的外壳设计和汽车外壳有相似性。用来掌握呼吸动作的系统,也类似于汽车的掌握系统。再者是电子系统、合成系统。把这些技能逐一分解就会创造,医疗东西和汽车有极大相似性,以是这两个行业的技能职员时常相互流动。医疗东西行业中,50%以上的人才不是出自医疗专业,而是出自汽车等设备行业。
10年中,我国的医疗东西行业,也经历了与汽车业类似的发展过程:早期没有自主研发的动力,由于不须要研发,复制国外产品也能活得很好。中国市场足够大,只要产品便宜、质量不差,企业就能分到一杯羹。
然而,拥有复制能力,却未必节制了核心技能。比如对呼吸机来说,核心是掌握系统。它可以在病人不能呼吸时帮助呼吸;但是当病人自己有一些呼吸能力后,又会逐步减少出宇量,让病人的自主呼吸逐渐规复。如果一台呼吸机,只知道不断给病人加气,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掌握系统设计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须要大量临床测试和调度。”吴东阐明,此类技能改进,不可能一挥而就,这便是国际大企业的“功底”。医疗东西面对的是生命,没有足够的临床验证,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轻易改动。她说,最怕的是复制国外的设备,却不理解为什么这样设计,复制时又想当然进行自作聪明的改动,那样更加危险,“还不如完备不动脑筋复制下来”。
在美敦力担当环球副总裁期间,吴东还兼任康辉集团总经理。康辉是海内有名的骨科企业,“但研发动力依然不敷,还是以复制国外产品居多。”吴东说。
医疗东西产品差异极大,既包括止血海绵,也包括医用磁共振成像等大型设备。根本领域涉及电子技能、打算机技能、传感器技能、旗子暗记处理技能、生归天学、临床医学、精密机器、光学、自动掌握、流体力学等。因此,医疗东西的发展受根本工业水平影响。美国、欧洲、日本由于发达的工业根本,长期处于天下领先位置。
多年来,我国高端市场险些被跨国公司霸占,海内企业紧张生产中低端、具有价格上风的产品,如中小型东西及耗材,仅有部分产品如监护仪、麻醉机、血液细胞剖析仪、彩超和生化剖析仪等具备出口实力。我们想要追上,非短韶光可以达成。
但是这次疫情,给了这个备受关注的领域一针“强心剂”。尤其是远程问诊、人工智能、无打仗自动化系统等,在疫情中大放光彩。医疗东西+新科技,在中国彷佛迎来了一个风口。
只有AI能做到
乔昕从事医学影像行业已有30多年。第一次听说数字医疗,还是10年前的事。
当时,几大跨国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数字医疗的潜力,比如一台CT机,在普通人眼里只是一个大硬件,但它的后台,实在有40种以上的操作软件,每一个软件都意味着一项技能。CT机的购买本钱中,软件占了一半。如果软件可以放在云端,供更多人免费***利用,那么采购本钱将会大为缩减。这便是“数字医疗”的发展潜力。
10年中,也有不少客户“吐槽”说,机器本身质量不错,便是软件操作起来非常麻烦,一点儿都不人性化。这些医疗软件须要受过演习的专业年夜夫才能操作。但实在,软件如果设计得更人性化、更便利些,对操作者的哀求就会降落,再结合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等技能,终极走向远程诊断、无人操作、人工智能的开拓方向,彷佛迎刃而解。
“医疗东西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大势所趋。”乔昕说,于是3年前,他毅然从天下500强医疗企业的高管岗位辞职,4个合资人一起成立了深睿医疗。
3年中,深睿医疗研制出了单器官多病种全肺AI产品,如炎性、肿瘤、肺气肿、胸腔积液、骨折等疾病等,结合深睿医疗的胸部平片AI赞助诊断产品,可对五大类30余种征象进行检出诊断。仅针对肺炎疾病一类,就有约14种征象识别,如磨玻璃影、网格影、胸腔积液等,而这些都与这次新冠病毒引发的炎症干系。疫情期间,这款AI产品在对新冠肺炎相似征象进行强化后,直接在武汉疫情中有了用武之地。比如说,早期很淡的肺部磨玻璃影,在疫情期间高强度的事情压力下,AI以其技能上风,可助力年夜夫减少漏诊。它还有一个独特的5次随访功能。比如,病人前一次的CT检讨显示,病灶占全肺体积的72%,这一次检讨占比85%……由此可以精确不雅观察疾病的发展过程,及时调度治疗方案。而这些精确的数据,用肉眼很难确认,AI做得更好。
疫情期间,深睿医疗先后向武汉各医院供应了40多套AI系统。曾为那位看夕阳的老人做事的上海援鄂医疗队也用这套系统帮助了许多病人。
那么,这套AI系统是如何研发出来的呢?
用大数据进行“培训”。设计者本身并不一定须要过硬的医学知识。大略来说,先找年夜夫,对每一个肺部影像进行读片,并标注上干系疾病,再把影像—标注数据输入打算机。当数据达到一定规模后,打算机可以根据这些大数据“深度学习”,不断自我优化。数据量越大,打算机学习韶光越长,判断结果也就越准。如今的人工智能读片准确率可以在98%以上,已经高于年夜夫的均匀水平。
两大上风得天独厚
清楚AI智能读片的研发过程,业内有一个普遍不雅观点——比较其他国家,中国研发人工智能医疗东西,拥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上风。
其一,中国有大量的数据样本。打算机须要大批数据,不断演习算法,许多国家没有如此大的人口基数,疾病的数据量受到限定。其余,当年夜夫数量不足多的时候,研发团队很难以得当的价格请大量年夜夫去做数据标注这种事情。
“我们的研发本钱中,至少有1/3用于数据标注。”一位研发职员阐明。比如,一个影像中的干系征象,至少须要2个年夜夫做标注,另2个年夜夫做裁判,一个影像须要至少4个年夜夫,这样标注出来的数据,才会相对准确,才有代价。而一些发达国家的人力本钱,可能支撑不了如此大规模的数据标注,研发受到掣肘。
其二,中国有广阔的运用处景。我们年夜夫的增长数量,远远赶不上病人的增长数量。面对数量弘大的患者、相对少的年夜夫,远程和人工智能诊断在我国有大量需求。
对有些国家来说,这项新技能则不是“刚需”。正常期间,一些国家的年夜夫可以花1小时只给1位病人看病。年夜夫本身也有当心生理,恐怕人工智能会威胁自己的地位和收入,以是国外的研发动力实际上并不敷。即便研发成功,推广也很难。
而我们的医患情形则与之不同。加上经由这次疫情的“大练兵”,海内已经开始批量考试测验人工智能医疗设备。几家海内企业几个月来订单量一贯上涨,有些企业的市值也因此翻了几倍。
“这种大数据、大场景运用,是许多国家不具备的。医疗东西+人工智能,中国确实具有弯道超车的条件。”乔昕说。
从大局来看,中国目前的医疗场景中,医药霸占较大比例,而东西利用相对偏小,依赖入口,价格昂贵。而发达国家医药和东西的运用差不多达到1:1。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医疗东西运用,未来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国际市场一贯认为,中国迟早会成为环球第一大医疗东西市场。这片尚未充分挖掘的蓝海,正等待着研发团队各显神通。
个中,上海发展医疗东西有自己的上风。
破题
长三角一体化
资深投资人高毅,长期深耕医疗项目,对该领域的未来,有一番自己的剖析和判断。如今,他拉着吴东博士和其他人,正预备组建一个国际顶尖的医疗东西团队,重点研发手术机器人。
手术机器人,可以看作医疗东西+人工智能领域的皇冠。它并不是生手以为的一种产品而已,它本身便是各种高新技能集成的一个大平台,涉及机器臂技能、光学技能、传感器技能、手术微创技能、互联网技能、人工智能技能等各种繁芜的系统,被称为“尖端高等机器人平台”。
国际上,在该领域有所建树的公司达芬奇,其高管曾经这样说过:“做手术机器人,就像做大飞机。”由此可见其难度和繁芜程度。
“此前,很多人以为只有超大型企业才有足够的资金与资源,乐意投入做这类具有繁芜系统的产品研发,实在从最近的20年环球科技革命历史看,原动力来源于快速发展的超级创新企业。”高毅说,环球巨子企业反倒没有足够的动力“自己革自己的命”,或者是“革得太慢”。从广为流传的柯达与数码相机的故事,到近在咫尺的特斯拉新能源汽车的案例,从中能清晰看到,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家当革命,每每不是由大公司自己主动发起的。
例如医疗东西革命性的下一拨浪潮:机器人平台,便是由达芬奇这样一个小小的项目开始的。它几经破产边缘挣扎求存,花了10年韶光,终于把产品推向市场,在医疗机器人领域独占鳌头。各大巨子这几年匆忙转向,虽奋起直追,但在浩瀚细分技能领域只能望洋兴叹。从长远看,机器人作为医疗东西的下一代聚合平台,只是刚刚开始。
直觉机器人(达芬奇母公司)在腹腔手术领域的巨大成功,吹响了医疗东西下一拨浪潮的号角。高毅认为,把握新浪潮的历史机遇,上海有得天独厚的三大上风。
第一,是国际化人才。吴东回顾起10年前研发中央选在上海的情由。她说,首先看大学,尤其是拥有多少所工科大学,这方面上海、北京具有明显上风。
第二,看家当链的集中程度。上海的汽车制造业更加成熟,机器人、自动臂等汽车家当发展上风明显。汽车工业造就了大批机器工程师、系统工程师、电子工程师、软件工程师,他们正好是医疗东西须要的专业人才。
第三,看医疗家当资源。特殊是临床资源,海内能比肩的仅上海、北京两地。大型医院浩瀚、顶级年夜夫聚拢,对医疗设备的临床研发特殊主要。上海传授教化类医院也多,意味着未来三五年,从前瞻性角度考虑,有潜力成为海内手术机器人领域的临床基地,培训出一大批接管前辈理念的年夜夫群体。
而上海的另一个上风是国际对外交流便捷,专家请进来、走出去都比较方便。
不过,如今,深圳有赶超之势。海内规模最大的医疗东西企业之一迈瑞,出自深圳恐怕并非有时。在电子软件上,深圳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电子零部件生产环境相对成熟。比较而言,上海有一个明显问题须要战胜:对制造业来说,租金本钱、人工本钱太高。如今,一些与机器人干系的大项目,企业会选择在上海研发,但在深圳生产。
“上海战胜本钱难题,可以从长三角一体化入手。”吴东说,上海主抓研发设计,由浙江、江苏等承担制造业的生产环节。江苏的模具、浙江的电器,都已形成各自成熟的供应圈。高毅认为,未来,企业可以在上海布局研发总部、临床中央和核心部件集成地,在长三角其他城市布局电子、软件系统,规模化建厂,形成一个长三角产学研体系。
医疗东西实质上还是制造业,如果无法战胜本钱和供应链难题,上海未来将会面临深圳的寻衅。
上海
建一座创新的生态丛林
临床资源和科研资源上,上海具备上风。不过投资人也有自己对一座城市的考量。
高毅认为,“新团队可以直接国际化”。如果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央,未来该当涵盖环球网络,把手伸出去,在外洋一起布局。尤其是当下,引进国外技能有很高的壁垒,但是国际化团队则无须地理空间上的引进,可以直接在当地转换成果,面向环球市场共同开拓,推出产品。如此也能用足上海的国际化上风。
值得上海重点思考的是,如何真正形成医疗家当链。本日企业在你这里落户,来日诰日别家有更优惠的政策,它很随意马虎就跑了。真正能让医疗企业落地生根、不愿再走的唯一情由是:这片区域有完全、成熟的家当链体系,高下游厂家高度集中,在这里,企业能便捷高效地找到各种互助伙伴。制造业不是单独一家企业的事,须要家当链高下游的技能协同。比如说人才政策,不仅仅针对重点企业本身,干系的高下游企业是否也须要同步扶持?
简言之,上海须要建立起一个创新的生态丛林,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生态体系。而政府就像一个超长期的计策投资人,保持耐性,孵化家当逐步成长,引发创新活力,这样与引进几家医疗企业比较,难度更大,但代价无可估量。
也有企业认为,技能成功并不代表商业成功。医疗东西前期推广时险些不计本钱,比如深睿医疗,捐赠给武汉的机器每台代价80万元。如今,大家看到了新技能的代价,而下一步是如何在市场立足,这须要政府更多的扶持。
实际上,上海对医疗企业的扶持程度已经很高,走在全国前列。深睿医疗在上海徐汇区的家当园设立分部近2年,与上海的干系部门、高校研究所、各大医院都建立了深度互助,也是上海人工智能大会的参与者、医疗板块分论坛的协办者。上海有关部门还为企业做了各种项目报告、推广,正因如此,“我们打算下一步把更多事情重心转移到上海。”乔昕说。
但是,险些所有采访工具都共同提及,上海对小微企业——即便是高科技型小微企业,扶持和重视程度依然不足。医疗东西企业研发总部达到300人以上,行业内已经算规模不小,但仍旧无法和互联网巨子、跨国企业比较。当医疗企业已经拿到了国家科技部的课题、国家自然基金的专项,在科技口对企业研发实力比较认同的情形下,产品真正落地时、推广运用时、探索商业模式时,创新扶持资源终极还是朝大企业倾斜。
此外,还有一种误解,大家总以为医疗领域的研发是一个口子的事。但个中的两个分支:药物研发与东西研发,是差别巨大的两类,所需的专业知识截然不同。前者侧重生物、化学,后者更侧重制造业、IT、大数据、人工智能。
而目前,海内医疗领域干系的政策,险些都把医药和东西放在一块儿,作为一个工具统筹。此前不少行业内人士都在呼吁,这样共用政策带来诸多不便。医疗设备、人工智能这类高科技领域,上海可以更多参与标准制订、家当政策制订。
归根结底,医疗机器人的浸染不是替代资深名医。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病人基数弘大的情形下,机器人的代价是供应更加安全、稳定的医疗做事保障,它也是办理这一社会难题的利器,乃至可以提升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
“国际同行认为,未来系统级医疗机器人的机会就在中国。由于我们这方面还是零起步,没有核心技能。”高毅说,环球医疗东西巨子们未来几年恐怕都会瞄准中国市场推出产品。而上海,建立全国乃至环球的医疗机器人中央,现在就得抓紧自己的机会。本报首席龚丹韵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