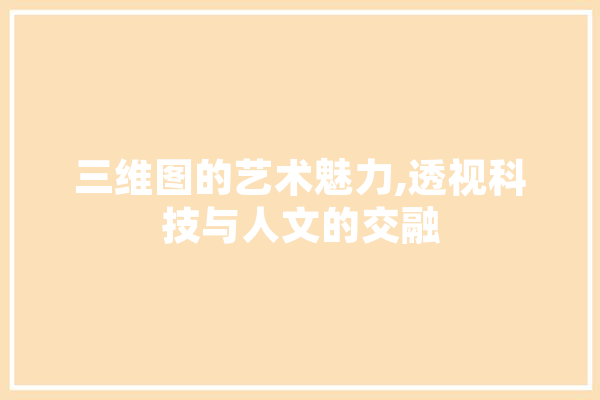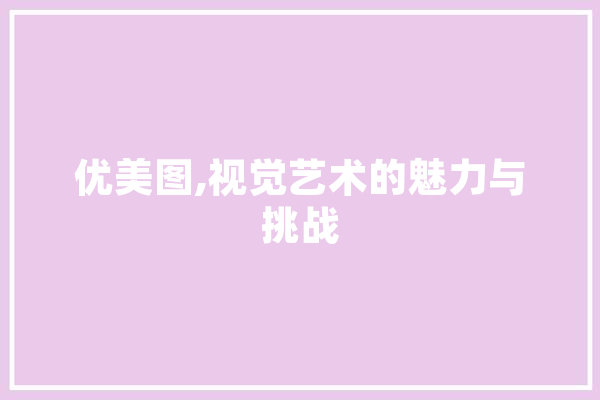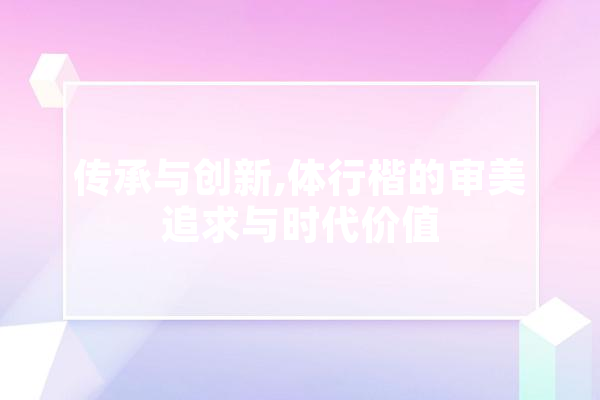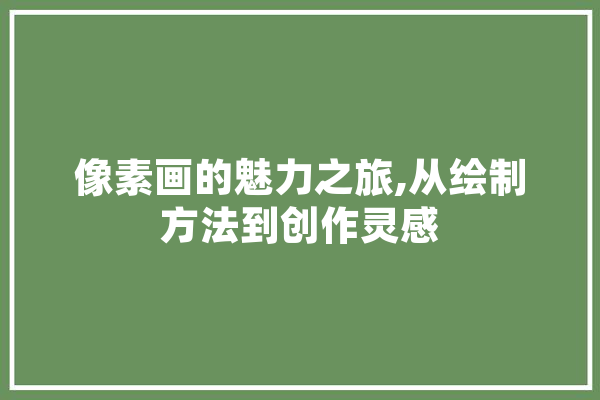5 位艺术家眼中的人工智能 | CCF-GAIR 2020_艺术_人工智能
一贯以来,面对技能的不断发展及其对艺术的影响,人类从未停滞对艺术和技能的关系进行探索和思考;但人类似乎从不担心自己对付艺术的专属所有权,毕竟,艺术来源于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想象力和创造力常日被认为是人类专有的。

但 AI 时期的到来,彷佛正在解构这一专属所有权。
仅仅从人类最为重视的创作领域而言,AI 已经在大量的艺术领域进行了原创性事情,包括 AI 绘画、AI 作曲、AI 唱歌、AI 导演、AI 写诗、AI 写稿、AI 雕塑、AI 平面设计……许多看起来不可替代的事情,AI 都可以完成,乃至在有些方面比人类做得更好。
是的,面对如此超越猜想之外的艺术动态,我们也是时候重新核阅 AI 与艺术的关系了。
作为海内最早关注这一轮 AI 技能变革与发展的媒体之一,雷锋网致力于对 AI 对全体社会发展各个行业和领域所产生影响的关注和宣布,这个中自然包括 AI 在艺术领域的进展和由此引起的思考。
2020 年 8 月 7 日至 9 日,由中国打算机学会 CCF 主理、雷锋网和喷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联合承办、鹏城实验室和深圳市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协办的 CCF-GAIR 2020 环球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峰会,在深圳成功召开。个中,基于当古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发展的最新态势,雷锋网特意在 8 月 9 日上午开设了 AI + 艺术专场。
在这一专场中,我们到了约请 5 位高朋,他们都是扎根艺术领域多年、但同时又密切关注着技能发展的跨界艺术家,并且都有着丰富的艺术理论和实践履历。他们分别是:
张海涛,策展人、艺术评论家、艺术档案网主编、天津美术学院硕导;
费俊,中心美术学院艺术与科技方向教授、某集体交互媒体创意总监;
郑达,跨媒体艺术家,“低科技艺术实验室”(Low Tech Art Lab)创立者;
王成良,中心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交通设计专业,交互艺术设计课程西席;
高峰,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博士后。
在现场,5 位高朋分别从艺术评论、艺术创作等角度,对艺术与 AI 等技能的关系进行了重新阐释,同时也先容了干系的跨界艺术实践;不同高朋不雅观点的激烈碰撞,竹苞松茂的艺术作品展示,以及深入浅出的艺术作品解读,令人眼界大开,思维震荡。
以下是本次大会的精彩回顾。
艺术评论家张海涛:自律与自省、希望与创造——机器人艺术学概论
策展人、艺术评论家、艺术档案网主编张海涛登台开场演讲,演讲的主题为《“自律与自省、希望与创造”——机器人艺术学概论》。
报告的开场,张海涛首先从一段波士顿动力机器人测试的***案例中提出了一个不雅观点:未来机器人艺术将成为科技艺术中最直接、最有活力的艺术媒介,从而给我们带来新的技能伦理的启迪,目前机器人还不具备反抗意识,近期被炒的很具争议的***中机器人对人的抗击是数字合成的殊效,不是真实征象,这一点已经得到科学界的证明。
张海涛回顾了机器人及机器人艺术发展的历史脉络,并谈到了在人工智能技能的加成之下,机器人将在多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详细来看:
政治领域:机器人未来如果一旦与人类的智能、意识等方面没有差异,乃至超越人类的时候,机器人可能会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和参政权;
经济领域:机器人会在经济领域产生高效的利润,社会构造将会发生根本性变革,许多职业都有可能消逝,由机器人霸占。
文化领域:会涌现人工智能哲学、文学、电影、艺术、建筑、伦理学等学科,改变我们的精神天下,人类从各方面对机器人产生高度的精神依赖性。
社会领域:未来我们需建构机器人的保护机制、领养机制、人机相互监督的机制,以及机器人身份、职业的设置,还包括与机器人干系的法律标准等。
而就机器人艺术来看,张海涛表示,它实际涌如今上世纪 50 年代,实在早于媒体艺术(60 年代涌现的录像艺术)涌现,那时候就已经有机器人绘画、机器人雕塑,后来也逐渐涌现机器人多媒体演出、机器人舞蹈乃至机器人评论家。由此,张海涛表示,现在的机器人艺术更方向于借机器人主体表达更多的不雅观念,对历史新的诠释或对未来的预见,以及对当下切身感想熏染的表达,而不仅仅只是对艺术本体媒介进行演绎,也便是说机器人艺术不能只勾留在让机器人画画、写字的低级阶段。
张海涛认为:
机器人智力的进化速率远远比人类进化的速率快多了,人类办理问题的能力和速率远远低于制造问题的进程,比如说生态毁坏和疫情、战役等问题,目前还没有能得到办理。人机和谐共处的条件便是让机器人不能象人类一样拥有私欲的原则下实现。由于机器人是人类创造的,以是将来涌现机器人报复人类的征象,还是人类自己的希望造成的。我们现在不能极度地认为所有科技本身有问题,很多技能是有益于人类的,但未来须要出台很多法律节制的源头是人类恶的希望,而不是科技的希望。
末了,张海涛先容了他在深圳华·美术馆策划的《机器·人·艺术·时期》展览,这一展览表达了机器人与艺术和时期的关系,也预示着机器人艺术时期的来临。
中心美术学院费俊:身体与媒体——智能科技时期的艺术与设计
接下来登台的,是中心美术学院艺术与科技方向教授、某集体交互媒体创意总监费俊,他为本次专场带来了题为《身体与媒体——智能科技时期的艺术与设计》的主题演讲。
演讲开场,费俊首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问题:
在这个由科技发展引发的 “身体缺失落” 年代,灵与肉是否可以独立存在?意识是否只能靠肉身来依托,还是可以用机器来承载?在数字科技时期我们还须要身体吗?人与机的边界在哪里?身体与科技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作为艺术家、设计师,我们在科技时期,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重新磋商身体和媒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有可能重启、重修、链接,乃至转化、延伸身体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由此,费俊通过一系列的作品磋商了身体与媒体之间的一系列关系,包括媒体对身体的改装、演绎、勾引、延伸、互动、链接等。
比如他参与策展的《戏游:探求生命中丢失的一小时》,是一个超过新媒体、戏剧、音乐与舞蹈的艺术现场。一个多小时的超日常场域体验,令怠倦而麻木的都邑人重启了尘封的身体感知,在探求韶光的路上,找寻丢失的自我。
在演讲中,费俊重点谈到了其在深圳华·美术馆展出的作品——《感情几何2.0》互动装置,这是他与数学家许晨阳以及生理学家刘政奎互助的跨学科实验作品。费俊表示:
数学的魅力和诗意在于,它可以用最大略且确切的办法,比如一段公式来阐明繁芜天下,代数几何数学家执着的追求用最极简的几何公式来描述繁芜的曲面几何。艺术的迷人之处是与其不愿定性有关的,我喜好用繁芜且混沌的的方法来表达这个繁芜的天下,用极简且确切的几何图形来表达繁芜且无常的感情数据,是作品《感情几何 2.0》的创作动机。
与费俊互助的生理学家刘正奎认为,生理学会把很多特殊的人算作是不正常的病人,但艺术界却会把这些人看作不平常的人,艺术的原谅性、参与性和表达性具有非常好的生理疗愈代价。
末了,费俊表示,无论是基于现场的作品还是艺术装置作品,都在呈现同样的愿景:
在这个身体缺失落的年代,艺术可以基于稠浊现实语境来重新构建人与媒体之间的交互界面,通过营造稠浊体验,把人们从伶仃、虚拟的天下再拉回到现实天下来,重新激活身体作为沟通介质的原力,更好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互关系。
跨媒体艺术家郑达:自然、传感器和互联——后人类时期的智能化艺术随后登台的,是跨媒体艺术家、“低科技艺术实验室”(Low Tech Art Lab)创立者郑达,他的演讲题目是《自然、传感器和互联——后人类时期的智能化艺术》。
演讲一开始,郑达基于自身经历,提出了诸多疑问,比如说:在同样的媒体文化和科技生态下艺术家和科学家在思考什么?视觉艺术家看到了什么?要创作出什么样的图景来描述当下人真是的生存状态?什么是 AI?艺术家如何看待数据和不可见的东西?
由此,郑达表示,这次在 CCF-GAIR 的人工智能前沿专场,大部分科学家谈人工智能都避不开打算机视觉,本日的 AI+艺术专场也是;机器人视觉作为 AI 科学研究的主要分支,如果只交给科学家来研究是不足的,真正理解图像、理解影像的,还是艺术家。
由此,郑达谈到:
人工智能的视觉识别发展到本日,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人类创造的图像或是机器创造的图像不再以人、艺术家为主体存在。比如说我事情室门口的门禁,开车进小区的时候摄象头可以捕捉、识别;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车牌号码、机器摄像头,它们相互的对视、相互的打算、读码和解码,这个过程和和人作为主体的天下已经没有关系的,机器自己产生图像、自己识别、自己判断,这是非常故意思的,其能力背后是从大量的数据集产生的。
由此,郑达认为,人工智能对艺术家来说,不是 PS 和工具,它让我们看到更多不可见的东西背后运行的办法。
基于这个不雅观点,郑达先容了一些与人工智能技能干系的艺术作品,来表现 AI 发展背后不可见的东西。他表示,艺术这个领域,我们一开始从科学性地描述自然,到现在科学性地描述不可见的层面,以是艺术家和科学结合得非常紧密,要善用各种工具。
因此,郑达也先容了自己位于武汉的 Low Tech Art Lab(低科技艺术实验室)和一些作品。比如说《机器的清闲之语》,这个作品来自于对人和机器自然交互的思考;当人摸它的时候,心跳的频率和曲线也会被科学性的描述出来,天生动画,这个时候机器的生命体征和人的体感同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瞥见智能化的机器。
末了,郑达表示:
对付我个人来说、对付低科技来说,我做的是把人和科技、不雅观众进行变置,分开原有的艺术创作机制,和机器之间的编码也是相互转换。我想说的是,艺术不仅仅是复制我们看得见的东西,还该当是把不可见的东西让所有人看得见。
中心美术学院王成良:影象设计——在人工智能领域下的勾引加接口设计随后登台的,是中心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交通设计专业的交互艺术设计课程西席王成良,他的演讲题目是《影象设计——在人工智能领域下的勾引加接口设计》。
在演讲开始,王成良率先提出了一个不雅观点:人工智能在艺术智能认知领域,比拟美术学院传授教化,基本上是勾留在本科二年级的造型设计阶段。
他表示,AI + 艺术实在并不算是主流,尤其是在国家目前的新基建大背景下,还没有参与到当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层面的需求。艺术被重新核阅之时,每每是在各种根本(新基建)达到一定积累完成之后才被在人文层面提出。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认知天下、不雅观察天下的方法是值得现在就开始去探究的,将如何映射给AI系统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眼下只有在动画片里实现了人工智能与艺术、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但眼下无论是新基建,还是 AI、5G 等,都无法实现这一点(目前还是处于功能型、只具备繁芜性掌握开关和较繁芜运算办法的凑集,与智能无通知样属于掌握论范畴)。
接着,王成良从自己在 2017 年央美给本科二年级开设的《勾引设计》这门课程的传授教化实践出发,谈到了自己对艺术与人工智能之间关系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人工智能艺术与设计所要研究的该当更多的是,如何映射艺术智能的思维方法、范式和数学模型给AI系统。在艺术事情中如何把艺术创造方法转化为、映射成智能,对付艺术生和艺术领域的事情实践来说,艺术和设计学习都有个范式,基本来说范式是存在于接口之中的,艺术家和设计师快速的思维变革,加上天马行空、异想天开的灵感等等办法……;打算机该当是不会明白和做到的,就算它能够与其它接口连接上,如: 3D 打印机,不同的数字形态设备和各种材料连接也是有局限的。这是艺术和人工智能的差异、人和人工智能的差异。
王成良表示,“勾引”和“影象”这两种方法论在艺术认知学习里是独特的,美术学院则是建构出来了一套单独的系统,和其他学科对这两个单词的认知和实践是有所不同的。其他学科有很多自己的影象方法、运算方法、勾引方法;到本日我们这个时期,这个须要碰撞共建出奇点的时期,更多的是须要接口设计,要探求和平衡这些相同点和不同点,不能成为任何一方作为主导范式的先入为主的思维排他意识。新的接口才能涌现所谓的智能大数据,而智能大数据的意义并不是一堆信息的堆放,而是如何进行更加精神性的超链接引发和启示。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能对话与面向高智能的互换学习。
末了,王成良谈到了未来人工智能时期人类和 AI 要办理三个问题,当它们都办理了,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人工智能,分别是:
“尊重”。首先要尊重一个物体、一个机器(AI),由于人工智能是有情绪的,要用一种新的互换规则与它互换,尊重它的理念,像人与人之间的互换关系;要尊重人工智能算法和运算出来的智能结果,目前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结果虽然不太令人满意(最多算是本科艺考之前考生演习可以达到的建构水平),但是我们还是须要尊重它的未来进化后智能运算的潜在巨大代价。
“信赖”。之古人们常常谈到无人驾驶汽车,我们如何把生命交给一个机器,这是须要一种在未来AI社会中、新的规则下已经建构出的全民共识和潜在的信赖;前两年还会有一些人提出异议,无人驾驶会不会侵害到人?在未来AI社会里,机器与人将建构出一种新的潜在信赖规则,人与人之间都不可能实现的互相信任,但却能在机器(AI)与人之间成为彼此之间稳定的信赖。
“共处”。人和机器 (AI) 在韶光上可以共处多久?一个家庭都不能共处一辈子,何况机器呢?人和机器 (AI) 怎么共处?如何开拓出共处生平的机器?机器 (AI) 要变革,人也要变革。人与机器(AI)可以事先就拥有一种共有的影象互换、终极为预想终点而设计闭幕,就像人生平的经历变革。
清华大学高峰:AI 重新定义艺术
末了一位登台的,是清华大学博士后高峰,他的演讲内容是《人工智能艺术与设计》,这也是高峰博士的紧张研究方向。
演讲开始,高峰谈到了自己对付科学和艺术关系的认知。他表示,科学和艺术实际上是非常紧密、不可分割的两个领域,艺术家的想象力每每启示着科学家的创造力;当然,艺术家也非常有创造力,科学家也非常有想象力;我们常常在一些科幻大片里看到艺术家、编剧、导演为我们勾勒未来的生活非常科幻,个中有一些已经逐渐变成科普,变成我们的生活,以是这是非常故意思的一个跨界领域。
谈到人工智能时期的艺术,高峰采取了自身在艺术实践中的一些案例,比如说让人工智能学习画家的风格,末了通过算法进行天生新的画作。
在这个环节,高峰先容了一个案例,也便是让人工智能和人类画家根据同一个主题——齐白石风格的虾——进行绘画,终极结果出人意料,齐白石最小的孙女齐慧娟女士评价称,人工智能绘画工具是她神往的赞助绘画工具,它可以很快提取画家的特点,成为一些想创作绘画的人的便捷工具和新的绘画路子。
在演讲中,高峰还引用了天下有名设计师唐·诺曼的采访,有提问人工智能是否可以设计出好作品,唐·诺曼回答称:
越来越多的产品已经由人机协同设计,机器、打算机发挥的浸染越来越大,包括人可以紧张做一些创造力、情绪干系的事情,而机器做一些重复性、噜苏、呆板的事情,人机结合往后,最有可能设计出好的产品。
接着,高峰先容了旗下的道子系统的人工智能虚拟形象,也便是道子白羽,它结合了古装和当代的风格,以小姐姐的面孔涌现,可以对话和交互,在前台、礼仪、接待都可以用这种设备完成很大一部分事情。
末了,高峰先容了自己的未来研究方向,包括脑机接口等。他认为,人机交互是通过鼠标、键盘、按钮、语音、触摸屏等等办法,这些都太繁芜。以互换为例,首先大脑掌握嗓子,把想法变成声音,声音进得手机里变成旗子暗记,旗子暗记通过网络传输到其余一个手机,手机接到旗子暗记往后再解码成声音,再通过喇叭、手机的扬声器播放出来,这个声音再进到耳朵里,耳膜振动才能听到声音,再经由大脑处理才知道:你想和我说这个事。
高峰表示,如果未来有脑机接口,中间所有的步骤省略了,设备插到脑筋里,两个人可以通过意念进行互换,很多科幻电影有两个武林高手,两个人面对面一动不动就有一方说我输了,这是他们在意念中仿照了一场比赛——脑机接口实现了往后,这有可能成为现实。
结语
一场论坛下来,艺术与 AI 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得到理解读。
但毫无疑问,科技与艺术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实际上,科学技能的发展,一贯在影响着艺术的变迁,乃至于,拍照、电影等艺术直接依托于影像技能本身的发展;而数字媒体技能和互联网的出身,也在创作、传播、接管办法、风格等多个维度上直接影响了艺术。
显然,AI 作为当古人类科学技能的最前沿,也给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极有可能是颠覆性的。
因此,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去看到 AI 与艺术的关系,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艺术家们对技能变迁的关注和深刻思考,也看到了艺术在 AI 科技发展中所绽放出来的崭新魅力;当然,从更深层的角度,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基于技能代价和艺术精神的人文关怀。
这大概便是我们开设 AI + 艺术专场的代价和意义所在——而 AI 与艺术的未来,也值得期待。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