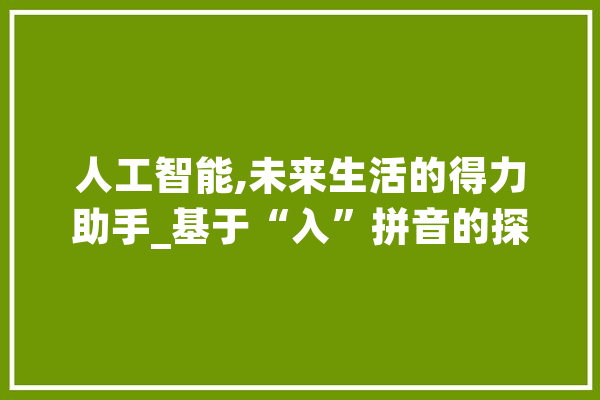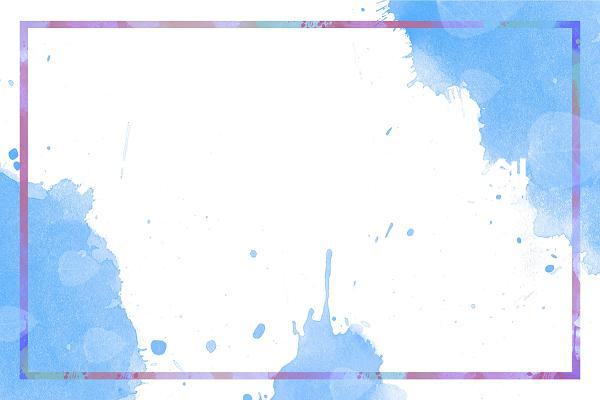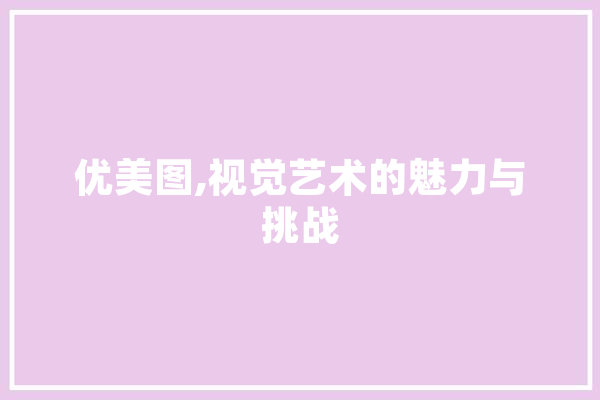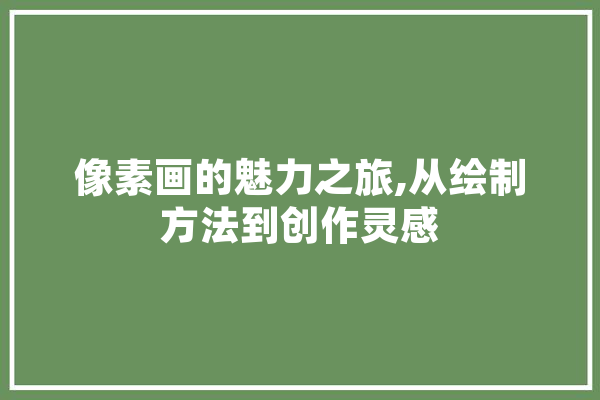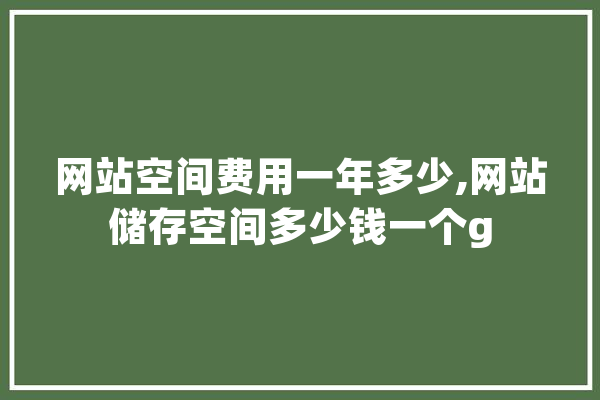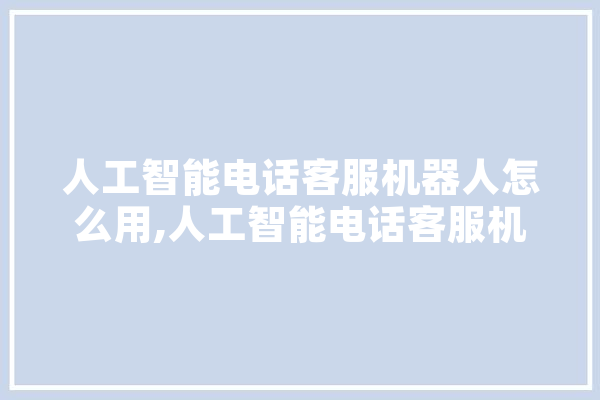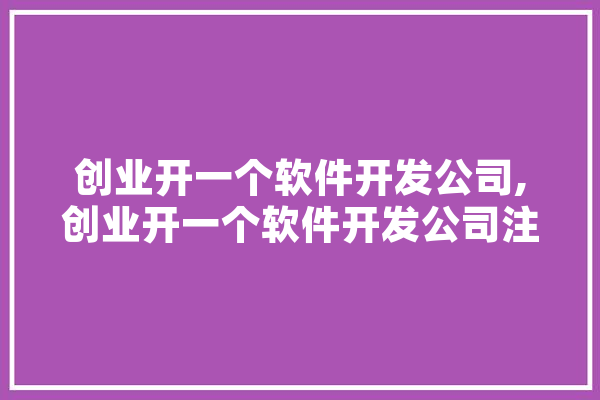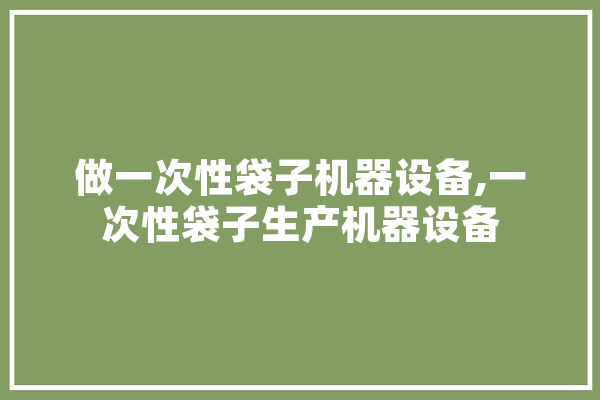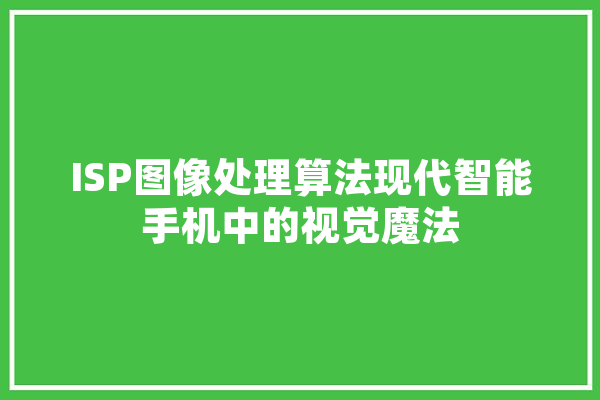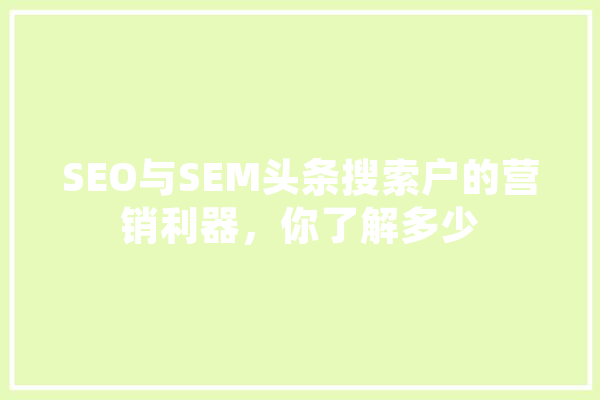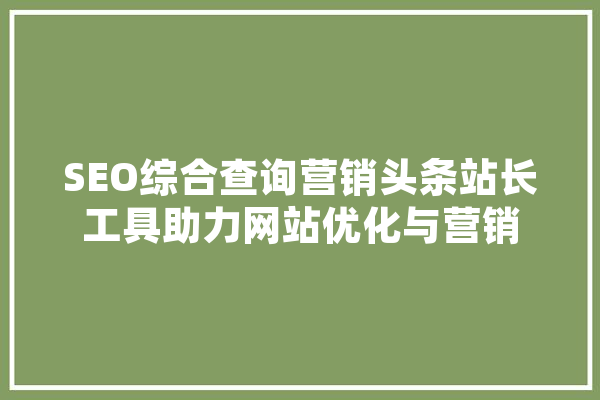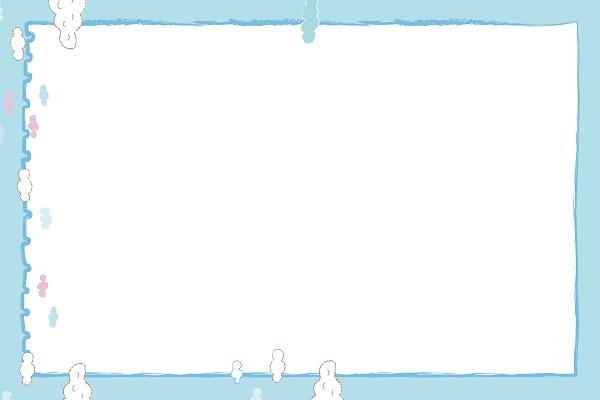从生成美学说起细数人工智能艺术的前世今生_人工智能_艺术
编译:lvy、橡树_hiangsug、蒋宝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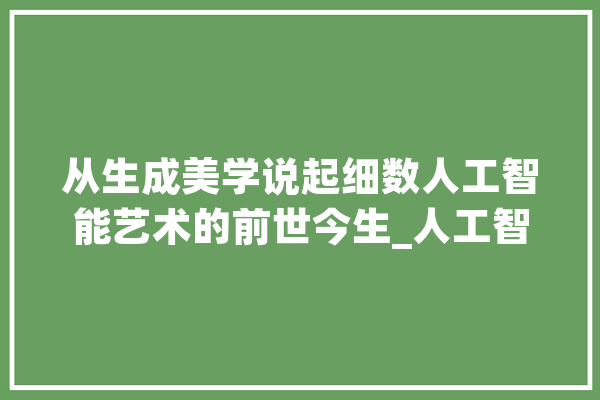
随着第一幅AI画作被拍卖了3000万公民币之后,机器艺术溘然变得炙手可热了。
许多博物馆和画廊已经在动手开办AI艺术作品展览。而国外一个名为9 GANs的艺术馆也将AI画作推向了市场。
不仅如此,一系列环绕着打算机艺术创作的哲学问题被不断激起,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实在大多数被称为“人工智能艺术特有的哲学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天生性艺术的前几次迭代中已经得到理解决。
换句话说:虽然人工智能艺术确实产生了新颖有趣的作品,但从艺术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并不像人们所吹捧的那样具有革命性子。
因此,人工智能艺术的未来与其说是将用于“图像制作”,还不如说是在为人工智能的工业化进程发挥其关键潜力。
前世:打算机艺术
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艺术家们就开始利用打算机创作作品。当时斯图加特大学马克斯本斯实验室的一组工程师开始进行打算机图形的干系实验,像Frieder Nake、Georg Nees、Manfred Mohr、Vera Molnr等艺术家也开始探索利用大型打算机、绘图仪和算法创建视觉艺术作品。
正如弗里德·纳克回顾的那样,最初这只是作为在本斯实验室测试新设备的练习,但很快就变成了一场艺术运动——马克斯·本斯为这种艺术形式供应了一个理论框架,并以此对立于法西斯主义。本斯认为,打算机艺术的字面上的“打算”美学故意避免所有的情绪诉求,从而使其免受政治攻击。
当然,从弗里德·纳克(Frieder Nake)早期对祖斯图形绘制仪的实验到海伦娜·萨里诺(Helena Sarinone)等当代人工智能艺术家的作品还不及完全半百之年的传承。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利用早期的打算机艺术实例来理解它,人工智能艺术就变得更有趣了。我们乃至可以说:早期的打算机艺术为当代人工智能艺术供应了缺失落的理论框架。
但为什么选择早期的打算机艺术作为参考,而不是像亚伦·赫茨曼(Aaron Hertzmann)提出的那样,选择电影或拍照?从表面上看,目前人工智能艺术的发展彷佛与拍照和电影的发展历史相似,它们都是从纯挚的“技能演示”开始的(想想著名的蒸汽铁路电影,听说是为了让不雅观众恐怖地离开剧院),经历了一个从模拟传统媒体(绘画和戏剧)到终极成为独立的艺术媒体的阶段。
此外,拍照和电影都具有漫长的历史可作为机器赞助艺术的理论参考,也很早就办理了机器的所有者问题:机器的所有者还是操作者拥有通过该机器创作的作品的所有权?
因此,拍照和电影对人工智能艺术看起来确实有借鉴意义。然而,打算机艺术与人工智能艺术有着更为明确和直接的联系:就像本日的人工智能艺术家一样,早期的打算机艺术家紧张关注的是大量的图像。早期的打算机艺术家认为作品的算法制作便是在创造“天生美学”。打算机艺术先驱弗里德·纳克在2010年一次清晰的采访中谈到了这个想法。
纳克的论点很大略:在打算机艺术中没有精品,由于打算机艺术不是关于“作品”的制作。它涉及到系统设计的产生,以及这些设计的都雅和同等性。换言之,对“天生美学”作品的审美判断机制是基于作品天生方法而非作品本身。只管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制造这种系统的工具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革,“天生美学”的思想仍旧存在。
例如, Alexander Mordvintsev的DeepStream(2015)作为机器学习的第一个艺术运用之一,实在质上是一个视觉转换系统(技能上基于特色可视化)。由于Deepdream紧张与imagenet/ilsvrc-2012(数据集)结合利用,因此天生了大量狗的形象,但Deepdream作为一个别系,它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数据集。事实上,DeepStream可以用来“find anything in anything”(译者注:即算法可以基于不同图像数据集创造出不同形象)。
一些对DeepStream的负面反响可能是由于系统没有利用不同的数据集发挥其全部潜力,在不反响其天生性子的情形下,将系统中的样本呈现作为全部事情的结果。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人工智能艺术所独占的,而是所有媒体艺术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且在市场压力下将持续存在——正如最近Deepdream被用来作为时尚模式的识别机器一样,这一问题再次被证明存在。
McDonald是2015年Google开源Deepdream后第一批考试测验Deepdream(除Alexander Mordvintsev本人)的艺术家之一。
如果我们现在把一些最盛行的作品命名为人工智能艺术,例如Anna Ridler, Sophia Crespo, Memo Atken, Mario Klingenmann, Gene Cogan和其他人的作品,那么很明显它们的作品实质上也是对特定图像集的操作:他们在通过图像数据集演习GAN(天生式对抗网络)隐空间,或通过各种方法探索这些隐空间的意义。从技能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早期的打算机图形学和当代的人工智能艺术都在对概率分布进行操控和探索。
这并不是说,人工智能艺术对艺术史没有任何新的贡献——只是人工智能艺术的哲学问题是历史问题,而不是当代艺术所特有的问题。然后,我们首先该当怎么定义当下时候人工智能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当代人工智能艺术对这些历史、哲学问题给出了什么详细的答案?
今生:AI艺术目前所面临的三大问题
人工智能淘金热是否来临?
最近有人提出一种不雅观点:人工智能迎来了“淘金热”。相对付环绕人工智能的极度媒体炒作,尤其是基于神经网络的人工智能艺术,实在人工智能艺术目前在已建立的艺术天下中的所占份额微乎其微。目前,人工智能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内部游戏,少量的主角带动了大量的审美和批驳输出。但这不一定是坏事,毕竟当代艺术的理念曾经意味着差异于大型机构和市场(即小众),而这一事实却在对当今人工智能艺术盛行的描述中很随意马虎被忽略。
拍卖会
支持“淘金热”的一个紧张案例是收藏家最近对所谓“人工智能艺术”作品的购买行为,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法国集体拍卖行在Christie’s以432.500美元的价格***了由GAN天生的罗比·巴拉特肖像中一个普通金边样品。
而在几周前,一个先前的版本实际以10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位私人收藏家。这在新生的人工智能艺术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当然,对已售出作品的重新拍卖感到愤怒是合理的,但这也同时表明人工智能艺术品的价格和数量并没有显示出所谓的“淘金热”。目前来讲,购买人工智能艺术紧张是一个宣扬的噱头,Christie’s借此得到免费公关的代价肯定比它臭名昭著地拍卖法国集体作品的售价赶过一个数量级。
切尔西美术馆曾开办过由Ahmed Elgammal主绘的Faceless Portraits Transcending Time show(无脸肖像跨时期展),正如美术馆老板菲利普•赫勒•古根海姆(Philippe Hoerle Guggenheim)直言道,该美术馆紧张是通过想通过之一类艺术展标榜自己身处站在前卫派的前沿中。
一些不雅观众认为人工智能艺术是一种威胁。在他的办公室里,霍勒·古根海姆给我看了一篇关于Instagram的评论,抱怨说这个画廊以机器创造的艺术为特色:“对付一个美术馆来说,真是太可惜了……他们居然不去支持人类视角下丰富多彩的天下(反倒去支持机器)。”考虑到人们对机器人从事人类事情的普遍恐怖,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些不雅观众可能会认为人工智能将取代视觉艺术家乃至所有人。霍勒·古根海姆反倒欣然接管了这一类批评——毕竟它只是表达了人们实际上对这一展会具有极大的关注度。
展览
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人工智能艺术展险些都是贸易展,基本上都是包含浅层机器学习知识的作品展览。而最近在伦敦巴比肯举办的“人工智能:超越人类”展览,很好地将技能,纯粹的装饰作品(如TeamLab的作品)以及人工智能艺术作品领悟在了一起。
这有助于再次核阅打算机艺术的历史,以理解展览策划人的折衷主义思想。伦敦(1968年)举办的神经机器奇缘展览是第一个展示技能性艺术的展览之一,它采取了同样的非观点来展示“统统技能”。
与巴比肯展览一样,它声称已经“创造”了技能在艺术中的运用,只管有很多早期的展览都这么说(如一年前萨格勒布和1965年斯图加特的展览)。然而,只有杰克·伯恩汉姆(Jack Burnham)在纽约犹太博物馆举办的软件展览会(1970年)开始关注利用技能所产生的详细问题,而不但是展示新技能。
杰克·伯恩汉姆在纽约犹太博物馆举办的软件展览会(1970年)
此外,从历史上看,技能演示和艺术作品的展示是相互穿插的。在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第二波媒体艺术高潮期间,技能演示非常狂热,许多策展人都将其作为展览的一部分,如卡尔·西姆(Karl Sim)的著名 “进化的虚拟生物” 展览(1994年)。
与此同时,克里斯塔·索默勒(Christa Sommerer)和劳伦特·米格诺尼尔(Laurent Mignonneau)等艺术家在技能期刊上揭橥了关于他们作品的文章,如A-Volve(1994年),并在Siggraph等技能会议上揭橥了演讲。
卡尔·西姆斯:进化的虚拟生物展览(1994年)
这两种征象,AI艺术展览的奇特概括,以及艺术品和技能演示的稠浊,都可以被视为艺术界缓慢采取某种技能的副浸染。然而,这种采取正在进行中,只是没有品牌作为AI艺术,作为一些最近由有名艺术家的作品显示。
人工智能艺术展览的兴起,以及艺术品和技能演示的领悟,这两种征象都可以被视为艺术界采取技能产生的副浸染。这种副浸染仍旧在连续,只能还没有在有名艺术家的作品中被标榜为人工智能艺术。
人工智能艺术能证明机器可以是艺术家吗?
在克里斯蒂丑闻事宜的谈论中,机器是否为艺术家问题引起了"大众年夜众的把稳,并被媒体和展览策划人欣然接管。事实上,机器可以是艺术家,乃至可以取代艺术家,就像他们将取代所有其他的事情一样。
但这种想法太空想化了,并不值得谈论:毕竟,创造艺术常日被认为是所有活动中最人性化的。但是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不雅观点:正如巴比肯展览中所展示的,人工智能终极会见告我们“是什么造就了人类”。在历史进程中,机器是艺术家一贯是打算机艺术的普通阐明。
弗里德·纳克(Frieder Nake)对20世纪60年代打算机艺术的这种思维办法提出了批评,由于这种思维办法很随意马虎与人工智能艺术产生交集:
当今画坛的进步与时尚服装和汽车界的进步是一样的[…]在我看来,“打算机艺术”不过是这些时尚中的最新一种,从一些有时中呈现出来,一时兴起的基于偏见和误解肤浅的“哲学”推理的主题,逐渐就会消逝,给下一个时尚留下空间。[…] 像“是电脑创意”或“是电脑艺术家”之类的问题不应被视为严重问题,句号。鉴于我们在20世纪末所面临的问题,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如果我们认为将人工智能艺术定义为GAN网络的创造,或者DeepDream的发展,那么这段话的别的部分彷佛非常得当。
接下来,如果我们再往前走,我们可以争辩说,机器和艺术家一样古老。艾伦·图灵在1950年著名的论文《打算机器与智能》中讲述了机器创造力的问题:
我认为,机器不能产生让人惊叹的不雅观点应归咎于哲学家和数学家特殊受制于一个谬论。这是一个假设,一旦一个事实被呈现给一个人,这个事实的所有用果都会随之产生。在许多情形下,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假设,但很随意马虎忘却它是假的。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人们假设仅仅通过数据和一样平常原则来办理后果是没有道德人性的。
换句话说,图灵认为,机器是否具有创造性问题的缘起是人们有一些刻板印象:即创造力与成果产出无关。基于图灵的不雅观点和对阿多诺的阐明,我们可以说艺术家是遵照直觉逻辑的,这是一个直不雅观的过程,但他们仍旧与理性过程一样受到规则约束。因此,机器具有创造性并不是例外,但是个中的规则约束和“机器能否创新”的问题源于有缺陷的创造性不雅观念。
正由于它有缺陷,机器是否为艺术家问题险些从来没有被人工智能艺术家自己提出过。克里斯蒂丑闻事宜,彷佛是人工智能艺术的技能参与,以及其对开源文化接管的一个实际产生的结果。而媒体艺术和打算机艺术传统上都没有开源代码/数据,因此它们没有碰着类似的问题。
人工智能艺术是“得当的”(当代的)艺术吗?
与艺术界的是否利用人工智能技能问题密切干系的是批驳性的接管问题。在对巴比肯展览的回顾中,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 )在《卫报》上写到了关于马里奥·克林格曼(Mario Klingemann)的作品《巡回演习》:
这是我所看过的最无聊的艺术作品之一。突变的面孔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表示出意义。很明显,复印机都比它们“智能”,由于在复印的过程中,复印机中可能还会有一些意外产生。
如果你看了上面对弗里德·纳克(Frieder Nake)的采访,这个不雅观点与20世纪60年代末的“我不太喜好它”非常相像。正如上面指出的,个中一个缘故原由当然是系统和人工制品的不同:克林格曼(Klingemann)的作品肯定不仅仅是一组可以单独判断的图像凑集。然而,琼斯(Jones)的评论(尤其是利用复印机的类比)针对的是人工智能艺术的一个特定问题:它的模拟性子。
模拟是一种和哲学美学本身一样古老的美学观点。它将审美过程描述为某种程度上仿照现实的人工制品的生产。众所周知,当代艺术试图从模拟中解放出来:首先考试测验抽象图像,然后完备摆脱图像(例如在观点艺术中)。当代艺术的核心并不图像的创造,这险些是一个完备缺点的发展,特殊是那些欣赏高度模拟艺术的博识技艺的人(例如,下面的古斯塔夫·凯莱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的作品),但事实上,这只是艺术界溘然意识到,它是19世纪末后迅速变革的天下的一部分。
比较之下,在本文谈论的有限范围内,人工智能艺术有一个问题:它基本上都是模拟的。毕竟,神经网络对天下的所有认知都来自它处理的数据。这里的“模拟”并不虞味着与(非抽象)拍照一样,人工智能艺术能以一比一的办法制造出与现实天下的人工制品相仿的作品。但是,它的输出仅限于其操作数据集的范围,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作品才有新颖性。举一个详细的例子:一个接管过梵高绘画演习的网络肯定会产生类似梵高的图像,但是它不会凭空产生一个图像,以是说,它反响梵高美学(印象主义)的艺术历史背景。一个神经网络永久不能与数据保持间隔,由于这些数据是它的全体天下,但这些数据仅仅是天下上许多子集中的一个,就像人类不雅观察者所看到的那样。
这也是为什么利用机器学习的艺术展示的“新奇效应”常常如此迅速地消逝。正如Zach Lipton所说的关于MuseNet:它“与我们演习LSTM天生__'的每个通用'完备一样无趣”。我认为这里没有任何音乐家该当感兴趣的内容。“纯粹的模拟,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但没有持久的审美代价。它可以轻松识别相似性,但很快就会消逝。换句话说,纯粹的模拟AI艺术变得非常快。
这也是为什么利用机器学习的技能演示的“新奇效应”每每会很快消逝的缘故原由。正如扎克·利普顿(Zach Lipton)对MuseNet的评价:“这与我们演习LSTM天生的每一种通用方法完备一样,是无趣的。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能让音乐家感兴趣的地方。”事实证明,纯粹的模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它没有持久的美学代价。它在识别相似性时供应了即时的知足感,但这很快就会消逝。换言之,纯粹模拟的人工智能艺术很快就变得庸俗。
上述人工智能艺术品交易的突出案例属于这一类。艾哈迈德·埃尔加马尔的作品乃至以“精心设计的框架”呈现,以“加强与欧洲艺术摇篮的联系”,如霍勒·古根海姆所说。很明显,也是这样。两人都***了名目繁多的历史肖像,这是一种几十年来都不属于当代艺术的作品风格——除了其对肖像的专门历史重构,如凯辛德·威利(Kehinde Wiley)所作的“古典的、欧洲的”彩色人像,这些人像永久不会涌如今“欧洲”中。“肖像”数据集。
上面提到的人工智能艺术交易的突出案例属于这一类。正如霍勒·古根海姆(Hoerle-Guggenheim)所说,艾哈迈德·埃尔加马尔(Ahmed Elgammal)的作品以“精心设计的框架”呈现,用来“加强与欧洲艺术摇篮的联系”。他们两人做了同样的事情,都***了名目繁多的历史肖像画,这种作品风格几十年来一贯没有成为当代艺术的一部分-除了专门的历史肖像重构,如凯辛德·威利(Kehinde Wiley)所作的“古典的、欧洲的”彩色人像。有色人种肖像,永久不会涌如今“欧洲肖像”数据集中。
Kehinde-Wiley的巴拉克·奥巴马肖像画:从欧洲肖像传统中接管了许多元素,同时批驳地超越了这一传统。
当然,与人工智能互助的艺术家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常常故意地在神经网络的模拟极限下事情。例如,海伦娜·萨林(Helena Sarin)纯抽象的GAN网络绘画,一些艺术家很清楚他们所选择的技能的历史意义。
这种意识在打算机艺术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例如,哈罗德·科恩(Harold Cohen)的“aarondrawing机器人”(aarondrawing robot),对纯粹模拟风格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索,是机器模拟能力边界上最突出的事情实例。
哈罗德·科恩,由AARON(1995年)创建的图像。
在海伦娜·萨林(Helena Sarin)的研究中,我们还创造了一种避免模拟的手段:手工致顿数据集。如前所述,DeepDream 是未来的工具包,它在imagenet/ilsvrc-2012之外还 没有充分发挥出潜力。数据集越有趣/精心策划,艺术就越有趣/繁芜。人脸会合成人脸,Imagenet会创造出狗,但是小的自定义数据集(结合精确的技能)会产生有趣的结果——正如萨林自己所说,在这一点上,险些所有的数据都是关于数据的。
未来:人工智能艺术的关键运用
这里有一个预测:一旦GANs成为得当的Photoshop过滤器,我们可以从David Bau(大卫·鲍)和其他人的作品中创造,模拟的问题会被办理。至少它将不再是人工智能美学探索的焦点,就像艺术访问互联网不再被视为网络艺术一样。
相反,艺术家们终极将接管人工智能艺术的关键运用:用人工智能批评自己。正如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在《The Author as Producer》一书中所说,技能性艺术的力量在于它能够站在生产关系中,积极地塑造某种技能的利用办法,而不仅仅是供应察看犹豫者的审美评论。人工智能艺术的未来已经开始了,一位从事机器学习的艺术家Kyle McDonald揭橥了一篇关于Gan天生人脸的顶级文章,如何识别人工智能天生的假图像。
换句话说,AI艺术将成为创新的驱动力,但正如五十年前Frieder Nake所提出的那样,不仅仅是审美创新的驱动力,而是批驳性创新的驱动力。正如抽象是对绘画中现实主义的批驳一样,人工智能艺术将成为批评“现实主义”人工智能的媒介,即人工智能在假设它是现实天下中的适当代理人的情形下利用(如有问题假设是 现实天下的有效和详尽的样本)。
换句话说,人工智能艺术将是创新的驱动力,但正如50年前弗里德·纳克(Frieder Nake)提出的那样,它并不是美学创新的驱动力,而是关键创新的驱动力。正如抽象是对绘画现实主义的批驳一样,人工智能艺术也将成为对“现实主义”人工智能批驳的媒介,即人工智能是在被假设成为现实天下中的一个适当媒介时才可利用的(就像ImageNet被假设是真实天下的有效和详尽的样本一样)。
总结
对付科学和艺术来说,这些都是激动民气的时候。然而,我们并不处于艺术革命的中期,更何况艺术家随时都有被机器取代的危险。常常被忽略的是(非平凡的)艺术的进步,就像科学的进步一步,建立在发明和创造的历史上,有的会渐进发展,有的会被质疑和推翻。
韶光将证明人工智能艺术是否会成为一场革命,它将质疑我们制作艺术的办法 - 但从一样平常的当代艺术史,特殊是打算机艺术史,这彷佛不太可能发生。更有可能的是我们本日已经看到的一个过程的延续:当代艺术对明确的“人工智能艺术”的修复。换句话说,机器学习将成为另一套工具。如果太过依赖这一工具,有关美学的哲学思辨将会逐步消逝。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