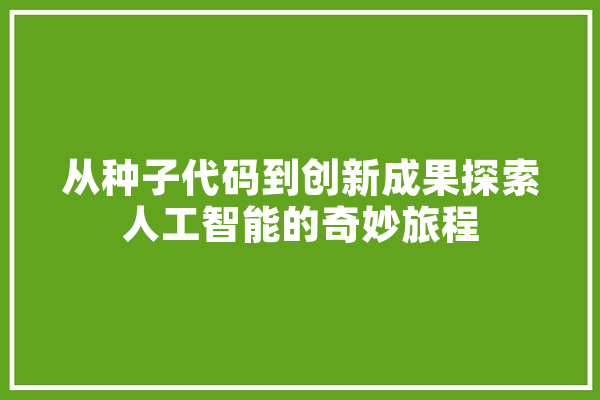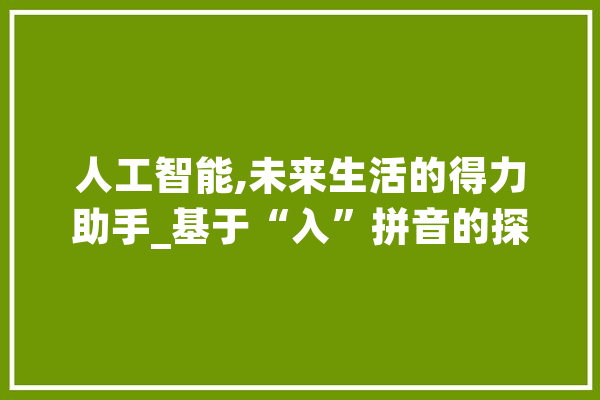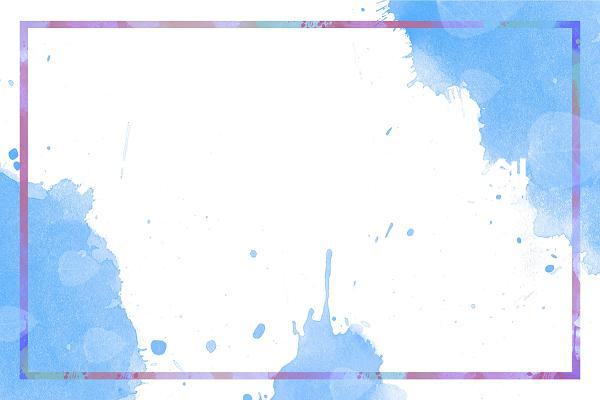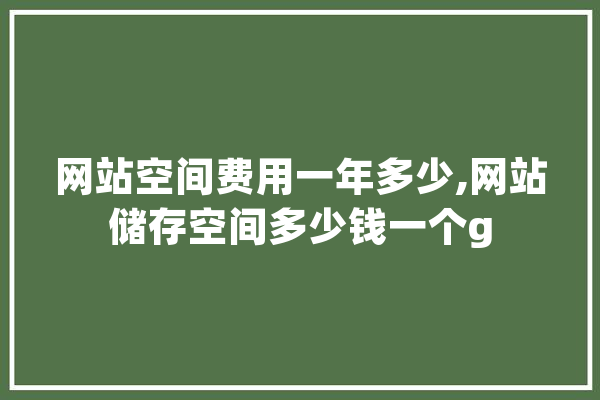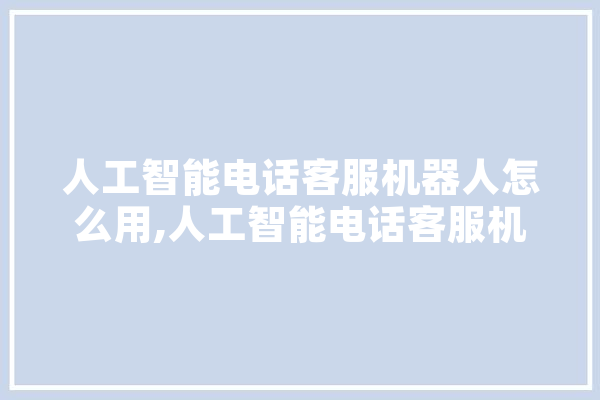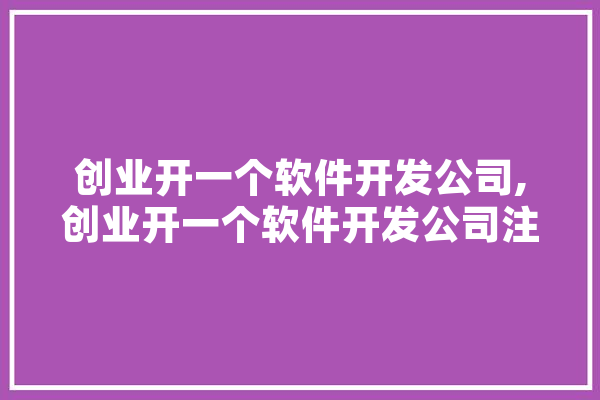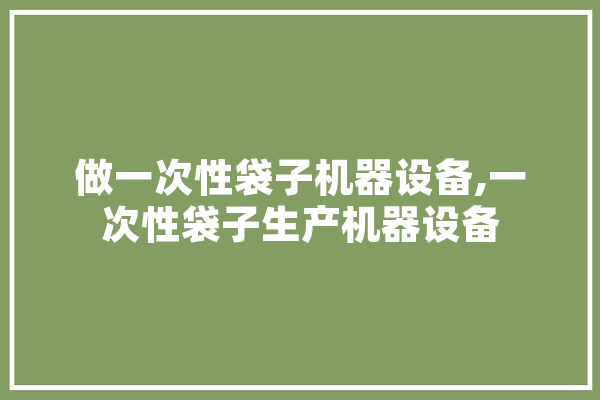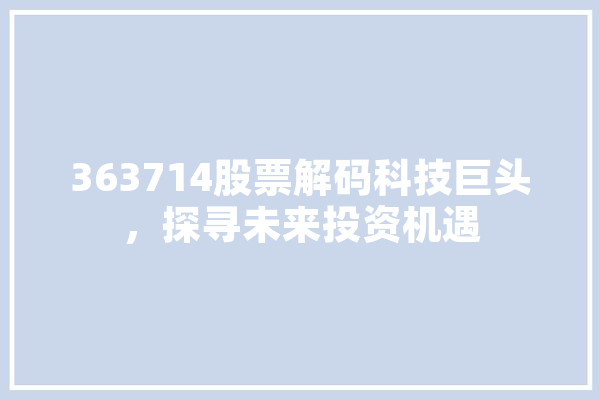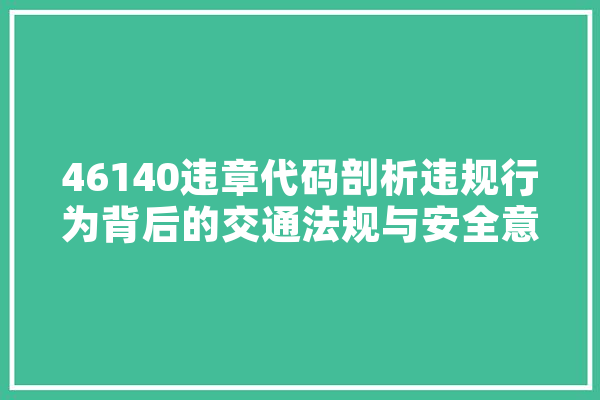人工智能会分开控制、息灭人类吗?_人工智能_人类
针对超级人工智能涌现后对人类产生威胁的话题已经旧调重弹了。已经有许多的专业人士正在就这一威胁可能带来的风险而进行研究了。人类的出路要么在于拥有一招关闭人工智能的法宝,要么在于让人工智能习得人类代价不雅观,或者研究所谓的友好型人工智能,但所谓的友好绝对不虞味着利他主义或者爱,而是指它们不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把我们消灭掉。本文作者Mara Hvistendahl,原文标题Can AI Escape Our Control and Destroy U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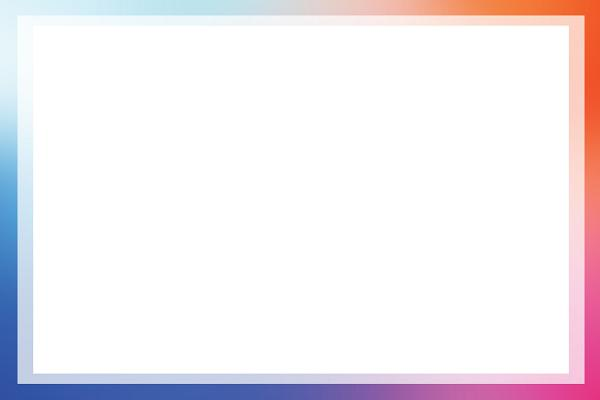
图片来源:Jeff J Mitchell/Getty Images
它开始于400万年前,那时人类的脑容量开始迅速攀升。五万年前,智人崛起。一万年前,文明开始发展。五百年前,印刷术的利用。50年前,打算机的涌现。还有不到三十年,它就会结束。
Jaan Tallinn在2007年的一篇网络文章《Staring into the Singularity》中看到了这段话。文中的“它”指的是人类文明。这篇文章的作者预测,随着人工智能的涌现,人类将不复存在。
Tallinn出生在爱沙尼亚,是一名打算机程序员,拥有物理学背景,喜好把生活当做一个更为宏不雅观的编程问题来看待。2003年,他与人共同创建了Skype,开拓了这款运用的后端。两年后,eBay收购了他的股票,他将其变现。如今他正在考虑再做点什么。《Staring into the Singularity》这篇文章里面不仅有打算机代码、量子物理等内容,乃至还有加尔文(Calvin)和霍布斯(Hobbes)的名言。他一下子就迷上了它。
Tallinn很快创造,这篇文章的作者、自学成才的理论家Eliezer Yudkowsky写了1000多篇文章和博客文章,个中很多都是关于人工智能的。Tallinn编写了一个程序,从互联网上搜集Yudkowsky的作品,按韶光顺序排列,录入自己的iPhone中。然后,他花了一年多的韶光阅读这些作品。
“人工智能”一词最早涌如今1956年,也便是第一台电子数字打算机问世仅10年后。有关该领域的预言最初都豪情万丈,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当早期的预测都没有实现时,人工智能的冬天来临了。当Tallinn创造Yudkowsky的随笔时,人工智能正在经历一场复兴。科学家们正在开拓在特定领域表现出色——比如会下棋、清理厨房地板和识别人类措辞——的人工智能。(此时间隔AlphaGo大胜人类不到10年。)只管下棋的人工智能不能扫地,也不能把你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但Tallinn相信,总有一天会涌现一种超级的人工智能,它会是一个集许多功能为一体的多面手,它乃至还可能利用随身携带智好手机的人天生的数据,在社交方面表现出色。
读了Yudkowsky的文章后,Tallinn相信,超级人工智能方面取得的“打破性进展”可能导致威胁人类的生存——人工智可能会取代我们在进化阶梯上的位置,像我们现在主宰猿类那样主宰我们,或者更糟的是,消灭我们。
在读完末了一篇文章后,Tallinn给Yudkowsky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用的都是小写字母,这是他的风格。“我是jaan,skype的创始人之一,”他这么自我介绍说,“我赞许……为人工智能超越人类这件事的到来做准备是人类的紧张任务之一。”他想帮忙。不久之后,当他飞往旧金山湾区参加其他会议时,在加州Millbrae的Panera面包店见到了Yudkowsky。他们的聚会持续了四个小时。Yudkowsky回顾道:“实际上,他对基本观点和细节有着很深刻的理解,这非常罕见。”之后,Tallinn给Yudkowsky供职的非营利机构——奇点人工智能研究所(Singularity Institut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开了一张5000美元的支票。2013年,该组织更名为机器智能研究所(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Institute,MIRI)。到目前为止,Tallinn已经给它捐赠了60多万美元。
与Yudkowsky的相遇给Tallinn带来了新目标,他决定肩负起把我们从自己的创造物中拯救出来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其他理论家和打算机科学家建立了联系,开始了他的旅行生涯,在世界各地揭橥演讲,谈论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不过,他紧张是开始帮助研究可能给人类带来出路的方法:所谓的友好型人工智能。这并不虞味着这类人工智能特殊善于评论辩论景象,或者它能记住你孩子的名字——只管超级人工智能可能确实能够做到这两件事。这也不虞味着它的动机是利他主义或爱。一个常见的谬论是假设人工智能具有人类的冲动和代价不雅观。“友好”实在意味着更基本的东西:未来的机器不会在它们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把我们消灭掉。
人工智能会威胁人类吗?在与Yudkowsky会晤9年后,Tallinn与我一起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Cambridge University's Jesus College)的餐厅用餐。教堂般的房间里装饰着彩色玻璃窗、金制的模型和戴着假发的人的油画。Tallinn坐在一张厚重的红木桌旁,穿着硅谷的休闲装扮服装:玄色牛仔裤、T恤、帆布运动鞋。
46岁的Tallinn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教科书式的科技企业家。他认为,由于科学的进步(只要人工智能不毁灭我们),他可以活“许多、许多年”。他对超级人工智能的担忧在他的同龄人中很常见。PayPal联合创始人Peter Thiel的基金会向MIRI捐赠了160万美元,2015年,Tesla创始人Elon Musk向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科技安全组织未来生命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捐赠了1000万美元。Tallinn进入科技这一领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一个同学的父亲在政府事情,让几个聪明的孩子有机会打仗到大型打算机。爱沙尼亚独立后,他成立了一家电子游戏公司。本日,Tallinn仍旧和他的妻子以及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住在自己祖国的都城(恰好也叫Tallinn)。当他想与研究职员见面时,他常日只到波罗的海地区。
他的捐赠策略也井井有条——就像他做的其他事情一样。他把钱分别捐赠给了11个组织,每个组织都在研究如何使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友好的不同方法,他希望个中某一个能坚持下去、产生结果。2012年,他与人共同创办了剑桥生存风险研究中央(Cambridg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Existential Risk,CSER),初期投入近20万美元。
生存风险——或者像Tallinn所说的X-risk——是对人类存在和延续的威胁。除了人工智能,CSER的20多位研究职员还研究景象变革、核战役和生物武器。但对Tallinn来说,其他学科紧张是帮助合法化失落控的人工智能的威胁。他见告我:“跟人工智能比起来,那些真的只是小巫见大巫。”对景象变革等更广泛接管的威胁的担忧,可能会吸引人们加入进来。他希望,超级人工智能机器统治天下的恐怖将说服他们留下来。他现在在这里参加一个会议,由于他希望大家能负责对待人工智能安全方面的话题。
我们的用餐差错都是随机参加会议的人,包括一位研究机器人的喷鼻香港女性和一位上世纪60年代从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男性。老人在饭桌上讯问每一个人他们上的是哪所大学。Tallinn的回答是,Estonia's University of Tartu,并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然后,他试图把发言引向***。Tallinn茫然地看着他。“我对短期风险不感兴趣,”他表示。
Tallinn将话题转向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威胁。当发言工具不是程序员时,他方向于打比方:超级人工智能可以像人类砍伐树木一样迅速地把我们办理掉。超级智能之于我们,就像我们之于大猩猩。为了面对可能到来的威胁,Tallinn认为我们得牢牢地联络起来。
每个人工智能都须要一个躯壳,老人表示,没有某种物理外壳,它怎么可能进行物理掌握?Tallinn回答道:“把我关在有互联网连接的地下室里,我一样可以会造成很大的毁坏。”
无论是Roomba还是它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后代,人工智能都是由结果驱动的。程序员会设定目标以及一系列关于如何实现目标的规则。前辈的人工智能并不一定须要被授予统治天下的目标才能实现它——它可能会在有时之中做到。打算机编程的历史上充满了引发灾害的小缺点和小有时。例如,2010年,一家共同基金公司Waddell & Reed的交易员卖出了数千份期货合约。该公司的软件在帮助实行交易的算法中漏掉了一个关键变量。其结果带来的是丢失万亿的“闪电般地崩盘”。
Tallinn帮助的研究职员认为,如果超级人工智能的褒奖构造没有得到恰当的编程,纵然是善意的目标也可能带来不幸的结局。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哲学家Nick Bostrom在他的著作《Superintelligence》中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台人工智能受命制造尽可能多的回形针,它可能会以为人体也可以算作原材料。
Tallinn的不雅观点自然也不乏批评者,乃至在关注人工智能安全的群体中也是如此。有人反对说,当我们还不理解超级人工智能时,担心它还为时过早。还有人说,把把稳力集中在泼皮技能行动者身上,会分散人们对该领域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的把稳力——比如大多数算法是由白人男性设计的,或者基于对他们有偏见的数据。“如果我们不在短期内应对这些寻衅,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个我们压根不想生活在个中的天下,”Partnership on AI实行董事Terah Lyons表示。该组织是一个关注人工智能安全和其他问题的多方利益干系者组织。但Lyons补充称,研究职员近期面临的一些寻衅——比如肃清算法偏见——是人类可能在面对超级人工智能时看到的一些寻衅的前兆。
不过,Tallinn并不这么认为。他回嘴说,超级人工智能会带来独特的威胁。终极,他希望人工智能社区能够效仿上世纪40年代的反核运动。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之后,科学家们联合起来试图限定进一步的核试验。“曼哈顿操持的科学家可能会说,‘看,我们在这里进行创新,创新总是好的,以是我们须要勇往直前’,”他见告我。
如何确保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安全不造成威胁?Tallinn警告说,任何确保人工智能安全的方法可能都禁绝确。他阐明说,如果人工智能足够聪明,它可能会比它的创造者更好地理解约束和限定。想象一下,他说,“在一群5岁的盲童建造的监狱里醒来,对付一个由人类制订约束的超级人工智能来说,情形可能便是这样。”
理论家Yudkowsky创造,有证据表明,这一点可能的确如此。由于,2002年起,他做过一个实验,自己在一个封闭的盒子里扮演人工智能的角色,而其他人轮流扮演看门人,卖力把人工智能局限在盒子里。五分之三的情形下,Yudkowsky——一个凡人——说服了守门人放他出来。然而,他的实验并没有阻挡研究职员考试测验设计一个更好的“盒子”。
研究职员认为,Tallinn正在帮助寻求各种各样——从实用的到看似天方夜谭的——的策略。有些人将人工智能理论化,要么构建一个实际的物理构造来支持它。其他人则试图教会人工智能坚持人类的代价不雅观。还一些人正在研究末了一招。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University of Oxford's 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FHI)的数学家兼哲学家Stuart Armstrong是一位研究这三种情形的研究员。Tallinn称该研究所是“全宇宙最有趣的地方”。(Tallinn已经向FHI供应了31万多美元。)Armstrong是天下上为数不多的全职致力于人工智能安全的研究职员之一。
一天下午,我和他在牛津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他穿着一件橄榄球衫,领口没有扣扣子,看上去就像一个一辈子躲在屏幕后面的人,苍白的脸被一团沙色的头发框住了。他在阐明中掺杂了令人困惑的大众文化背景和数学知识。当我问他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取获胜利可能是什么样子时,他说:“你看过乐高电影吗?统统都太棒了。”
Armstrong的一项研究着眼于一种称为“oracle”人工智能的特定局限方法。2012年,他与FHI的联合创始人Nick Bostrom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不仅要把超级智能隔离在一个储罐中——这是一种物理构造——还要把它限定在回答问题上。但纵然有了这些界线,人工智能也将拥有巨大的力量,通过奥妙地操纵守门人,重塑人类的命运。为了减少这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Armstrong发起对对话进行韶光限定,或者禁止提出可能颠覆当前世界秩序的问题。他还建议,让oracle通过指数来衡量人类的生存状况,比如道琼斯工业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或东京的过街人数。
Armstrong在一篇论文中称,终极有必要创造一个“大赤色关闭按钮”:要么是一个物理开关,要么是一个被编程进人工智能的机制,在以便在最紧急的关头对人工智能进行关闭。但设计这样一个开关远非易事。一个对自我保护感兴趣的高等人工智能不仅可以阻挡按钮被按下,它还会好奇为什么人类会发明这个按钮,大概想要激活它看看会发生什么,然后让自己报废。2013年,一位名叫Tom Murphy VII的程序员设计了一款可以自学玩任天国娱乐系统游戏的人工智能。为了不输掉俄罗斯方块,人工智能按下了停息键,让游戏保持冻结状态。Murphy在一篇关于自己的造物的论文中挖苦道:“说真的,唯一的制胜招便是不玩。”
要让这一策略成功,人工智能必须对按钮不感兴趣,或者,正如Tallinn所说,“它必须对它存在的天下和它不存在的天下授予同等的代价。”但纵然研究职员能做到这一点,也存在其他寻衅。
最令研究职员愉快的方法是,找到一种让人工智能坚持人类代价不雅观的方法——不是通过编程,而是通过教人工智能学习代价不雅观。在一个党派政治占主导地位的天下里,人们常常会放大我们的差异。但是,Tallinn指出,人类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能够被教会识别这些不可改变的规则。”
在这个过程中,人工智能须要学习并欣赏人类不合逻辑的一壁:我们常常说一套做一套,我们的一些偏好与他人发生冲突,以及人们在喝醉时不那么可靠。但我们所有人在运用程序和社交媒体上留下的数据轨迹或容许以供应一个指引。Tallinn认为,只管面临寻衅,但我们必须考试测验,由于意外验测验的风险太高了。他表示:“我们必须提前思考几步。创造一个与我们兴趣不同的人工智能将是一个恐怖的缺点。”
人工智能须要意识吗?Tallinn在剑桥的末了一晚,我和他以及两位研究职员一起在一家英国牛排馆共进晚餐。一个做事员把我们这群人安排在一个粉刷成白色的酒窖里,酒窖里有一种洞穴般的气氛。他递给我们一页菜单,上面有三种不同的土豆泥。一对夫妇在我们阁下的桌子旁坐下,几分钟后哀求搬到别处去。“我觉得太幽闭了,有点胆怯,”这位女士抱怨道。我想起Tallinn的那些话,他说纵然自己被锁在一个只有互联网连接的地下室里,同样可以造成毁坏。
Tallinn的客人包括前基因组学研究员Seán Ó hÉigeartaigh,他是CSER的常务理事,以及Matthijs Maas,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人工智能政策研究员。他们开玩笑说,要拍一部名为《Superintelligence vs Blockchain》的书呆子动作片以及开拓一个名为“Universal Paperclips”的在线游戏,还原了Bostrom书中的场景。这个练习包括反复点击鼠标来制作回形针。这并不是什么华而不实的东西,但它确实解释了为什么一台机器可能会探求一种更简便的生产办公用品的方法。
终极,发言转向更大的问题,就像Tallinn在场时常常做的那样。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创造出像剑桥大学哲学家、CSER联合创始人Huw Price曾经说过的那样,“在道德和认知上都是超人”的机器。其他人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想让人工智能主宰我们,那我们想主宰它吗?换句话说,人工智能有权利吗?Tallinn说,这是一种不必要的人格化。它假定智力即是意识——这一误解惹恼了许多人工智能研究职员。当天早些时候,CSER的研究员Jose Hernandez-Orallo开玩笑说,当与人工智能研究职员交谈时,意识是“C-Word”,而自由意志是“F-word”。
现在在地窖里,Tallinn说意识无关紧要:“以恒温器为例。没有人会说它故意识。但是如果你在零下30度的房间里,和人工智能对质真的很未便利。”
ÓhÉigeartaigh表示:“担心意识产生的影响是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没有首先办理技能安全方面的寻衅,我们就没有那么多韶光担心意识带来的问题。”
Tallinn表示,人们过于专注什么是超级人工智能,它会是什么样的,我们该当担心一个人工智能,还是一群人工智能?他强调:“在我们看来,主要的是人工智能做了什么。”他认为,就目前而言,这可能仍取决于人类。
译者:喜汤
【用户调研】
为了供应更优质的文章与用户体验,我们正在进行关于36氪号的用户调研,诚邀您花几分钟韶光帮忙填写这份问卷,感激!
请戳:https://www.wenjuan.com/s/IfaYra/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