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早期人工智能哲学研究_人工智能_哲学
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的起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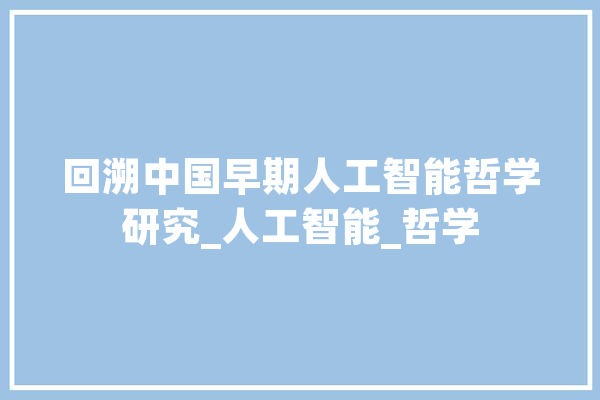
人工智能哲学在中国是如何起源的?人工智能本身存在两条线索:一条是从“智能”到“人工智能”的观点起源;另一条是从掌握论到人工智能的理论起源。“人工智能”观点的涌现可追溯至20世纪60—70年代。1965年,《自然科学学科简介》在“打算技能”一级条眼前设有“信息加工理论”二级条款,后者下设有“人工‘智能’研究”三级条款。1972年,《仿生学文献索引(二)》内已明确利用“人工智能”对应于“Artificial Intelligence”,并列有一样平常问题、自组织、学习机、考试机及其他有关装置等子条款,是目前可见最早利用“人工智能”的中文文献记录。
此外,虽然比较于本日,半个多世纪前的打算机技能水平较低,然而机器仿照人类智能(或者说机器仿照大脑)的主要发展目标,自那时起便已树立起来。从实践上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前行的,这天益发展的打算机技能;而从理论上联结起“人工”与“智能”的,是具有横断性子的科学——掌握论(Cybernetics)。人工智能起初被视为掌握论的弘大科学体系的四大分支之一(其余三个分支是工程掌握论、生物掌握论和社会掌握论),也是掌握论沟通“实质上不同的技能系统、生物界和社会”的一种表示。
正如“老三论”(系统论、掌握论、信息论)的科学研究与其哲学研究之间具有联动效应一样平常,中国人工智能研究的开启与人工智能哲学的兴起也是同步的。20世纪60—70年代,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研究紧张表现为少量的翻译和零散的谈论,到改革开放后才渐趋火热起来。70年代中后期前,《自然辩证法杂志》与《摘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系列翻译了苏、美、日、英、德、法等多国学者的研究论文。由于时期的分外性,当时以对人工智能的哲学批驳为主,如认为“从‘人工智能’中可以嗅到唯心论和玄学天下不雅观的腐烂气味”。到了70年代末,除了《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等自然辩证法界刊物,《哲学研究》《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等综合性哲学刊物也纷纭将人工智能哲学纳入视野。
从学科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哲学的起步与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自然辩证法(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十二年(一九五六—一九六七)研究方案草案》在第六类题目“数学中的哲学问题”内已列有“掌握论中的哲学问题”。《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发展方案纲要(草案)》则在第六项“各门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内明确列出:“在技能科学方面,例如要研究人工智能、掌握论、信息论和仿生学中的哲学问题,对系统工程学的剖析等。”
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热潮
20世纪80年代,人工智能哲学在中国掀起了第一波研究热潮。这股热潮的推动主体有两个哲学分支学科:一是引领人工智能哲学的自然辩证法,二是拓展人工智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为代表,包括陈步、童天湘、范岱年、丁由等在内的前辈学者,有关事情涵盖论文、期刊、会议、组织等多个方面。1981年,社科院哲学所、中科院自动化所、中科院生理所联合举办了“人工智能哲学问题漫谈会”,是首次专门的人工智能哲学学术会议。参会者来自不同单位,涵盖哲学、打算机科学、生理学、措辞学、情报学等多个领域,被评价为“自然科学事情者和哲学事情者结成同盟”。同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虽然该学会因此自然科学事情者为主的社团组织,但起初挂靠在社科院,童天湘当选为副理事长,反响出人工智能哲学对全体人工智能领域的强大影响力。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也密切关注人工智能这一科学技能发展的新征象,20世纪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论著每每会专门提及人工智能哲学,从而使人工智能哲学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时期性和综合性的新兴哲学主题。由浩瀚不同形式的造诣搜集起来的这波热潮有其焦点——认识论,并可细分为三大主题。
其一是紧张问题——思维与物质的关系。机器仿照大脑亦即机器仿照思维,也是人工智能哲学的初始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人工智能是“在理论和运用两方面并行探索”,紧张有自然措辞处理、定理证明、感知问题、制造自动化、专家咨询系统等。根据人类思维的特点,人工智能须要占领两个难关:一是认清作为思维器官的大脑,二是使机器具备人类思维的自我学习能力。人工智能若能实现机器仿照大脑,也就意味着物质能够仿照思维。这种仿照是物质对思维的“再现”,“肃清了精神的神秘性,在认识论上是一个打破”。
其二是关键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曹伯言、周文彬提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生产和科学技能发展,使人工认识器官不再局限于认识工具的范畴,而可能成为认识主体。只不过,人工主体不具备社会性和阶级性。这一论点有着较大反响,童天湘和王海山分别撰写了与之商榷的文章。1981年5月、6月和11月,《哲学研究》编辑部先后在上海、大连和北京组织召开了三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当代自然科学”漫谈会,对“人工认识主体”的探索和争鸣余波不断。
其三是经典问题——人与机器的关系。人工智能的技能形态也是机器,但却已从根本观点上差异于以往的机器,如与之干系的“机器人”“电脑”等名称。“人工智能”本身亦是如此,“人工”表明机器属性,“智能”则被预设为与人类智能相同或相似。机器人能否等同于人?电脑能否等同于人脑?人工智能能否等同于人类智能?在18世纪哲学中,“人是机器”引起了许多辩论;而在当代哲学中,“机器是人”也同样引起了许多辩论。人工智能哲学可以实现人与机器关系问题的主客颠倒,即从“人是机器”到“机器是人”。一旦“机器是人”成立,人与机器的关系就不仅是人与技能工具的关系,也不仅是人与技能实体的关系,还是人与“技能他者”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转向
20世纪90年代往后,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研究的整体热度稍降,发生了研究关注点切换的“社会转向”。人工智能哲学研究的视野转向了人工智能与社会,磋商人工智能与时期变革、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人工智能与社会生产等话题。
童天湘的先驱性探索便是“社会转向”的代表,紧张有《智能革命论》(1992)和《点亮心灯——智能社会的形态描述》(1996)两部著作。在他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环绕智能形成新一代的生产力,这种新的生产力拥有“人机复合智能系统”的紧张形式和“高智力和高智能机(器)”两个要素。新的生产力推动形成新的生产关系,终极将创造出新的社会形态——智能社会。农业社会以生物为紧张资源,工业社会以技能为紧张资源,智能社会将以智能为紧张资源。为欢迎正在发生的智能革命和即将到来的智能时期,人工智能哲学也要作出超前的反思。
作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奠基者之一,马希文在哲学领域的贡献亦值得纪念。他参与译校了德雷福斯(Hubert L. Dreyfus)的《打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1986)和侯世达(Douglas R. Hofstadter)的《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书——集异璧之大成》(1997),两者的原著与翻译均堪称经典。2003年出版的《逻辑·措辞·打算——马希文文选》不仅收录了他的各种研究作品,而且通过副标题关键词概括了他的研究旨趣。他认为,“打算机便是当年的蒸汽机”,应关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期所发生的变革。“打算机不应是也不会是终极的智能机器”,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就纵向而言,“社会转向”开启了当今人工智能哲学的潮流,与本日学界习气于从科技伦理、社会管理等角度切入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办法具有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回顾20世纪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的发展进程,可以总结出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在60—70年代逐渐起源,在80年代趋于兴盛,在90年代发生转向,从而共同构成21世纪人工智能哲学在中国进一步提升广度和深度的根本。
从20世纪中国人工智能哲学研究本身具备的多少特色来理解,可总结出以下三点。一是根本性。以“机器能否仿照思维”“机器如何仿照思维”“机器对思维的仿照能到何种程度”等问题作为人工智能的出发点。这些既是科学问题,也是哲学问题。乃至可以说,人工智能哲学研究起初就紧扣哲学基本问题,关注如“思维与物质的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等问题。二是综合性。对付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不但是全体哲学界的发力点,尤其是表现突出的自然辩证法界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而且是哲学以外的领域所感兴趣的,参与人工智能哲学学术研讨和翻译事情的还有打算机科学、生理学、措辞学、情报学等领域不少跨学科研究者。三是前瞻性。只管人工智能哲学立论的根本可能只是逻辑上或理论上的可能,但这类理论磋商的代价仍是值得肯定的。近年来的人工智能哲学在热度上无疑超过了20世纪,但就研讨哲学基本问题、联合不同学科尤其是科学界、研判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未来社会管理等方面而言,仍可从中得到启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智能革命与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的哲学研究”(17ZDA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雷环捷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