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简史-人工智能简史读后感_人工智能_哲学
文 | 徐英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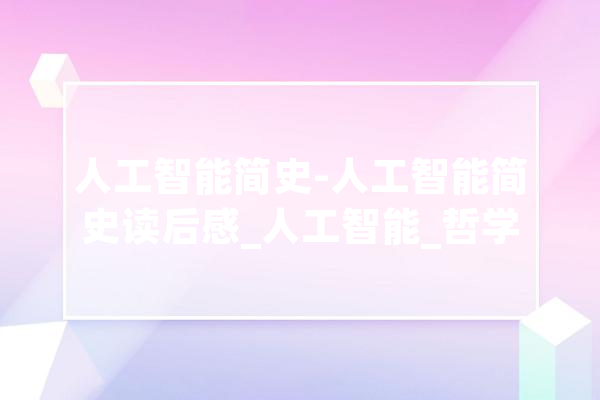
最近,Nick师长西席写了一本新书,书名是《人工智能简史》(公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12月)。由于我近十年来一贯从事人工智能哲学的研究,自然也买一本尽快看完。在这篇书评中,我想特殊谈谈这本书的第9章。该书的第9章“哲学家与人工智能”,紧张是为寻衅哲学家,尤其是那些对人工智能有话要说的哲学家而写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海内大多数理工科研究者对哲学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即:哲学家不应该干涉我们的地盘。
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对付哲学家是否有资格对科学问题揭橥评论,我以为自己确实有话要说。我承认,哲学家并不是对所有科学和工程问题都有话要说。比如,哲学家不会对“歼-20为什么采取鸭式布局”的问题揭橥见地,至少作为哲学家不会。但对付“进化论能否运用于生理学领域”、“量子力学的实质是什么”等科学家未必有明确见地的问题,生理学哲学、生物哲学、物理学哲学肯定有话要说。很多人会问: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你有什么资格对这些问题揭橥评论?答案很大略,在国外,处理这些问题的哲学家每每拥有两个以上的学位。 比如神经哲学的专家保罗·丘奇兰德和帕特丽夏·丘奇兰德,他们都有很深的神经科学背景,纵然你看到一个只有哲学学位的中国学者对一个科学问题揭橥了拙劣的辞吐,你也不能就此推断这个行业整体上不好,由于事实可能只是这个行业的专家不在你的朋友圈里。
按照同样的逻辑,哲学家当然可以在人工智能问题上发言。缘故原由很大略:符号人工智能和联结主义人工智能对付什么是智能的基本定义都不清楚,解释人工智能怎么做,业界还没有统一的见地。听听哲学家的见地,大概也不错。有人可能会问:问题是哲学家连一行程序都不会写,我们为什么要听哲学家的?两个回答就足以回嘴这个问题。
波洛克
第一,怎么知道哲学家不会写程序呢?比如认识论研究的重量级学者约翰·波洛克,就曾开拓出名为“奥斯卡”的推理系统,干系研究成果揭橥在主流人工智能杂志上。再比如,当今英美哲学界享有盛誉的心灵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是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人工智能大神霍夫施塔特的弟子,曾随老师揭橥过人工智能论文。难道他不会写程序?
第二,对人工智能揭橥见地,是不是必须会写程序才能揭橥见地?作为低级操作,编写详细代码类似于军队中最大略的射击动作。但请大家想一想:毛泽东能降服蒋介石的百万大军,是由于有运筹帷幄的能力,还是由于他精通射击?答案无疑是前者。显然,哲学之于人工智能的低级操作,就犹如毛泽东的计策思想之于射击等战术动作。
查尔默斯
但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尼克师长西席显然不像我一样重视哲学家。他在书的第九章中列举了三位与人工智能有交集的哲学家,并逐一进行了批驳。第一位是试图借助海德格尔思想资源批驳符号人工智能的征象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第二位是试图通过“中文房间”论证回嘴强人工智能可能性的措辞哲学家约翰·塞尔;第三位是试图通过“碗中大脑”思想实验证明语义外在主义精确性的剖析实用主义者希拉里·普特南。但从论证的角度看,尼克的干系谈论显然存在“归纳不充分”的风险:这三位哲学家能否代表哲学界对人工智能的普遍意见?比如,作者对上文提到的查尔默斯和波洛克只字未提。 以作者提到的塞尔的“中文房间”思想实验为例,他彷佛完备忽略了与论证干系的一个基本事实:网上能找到的数百篇评论塞尔思想实验的英文哲学论文,大部分都是对塞尔的批评。在这种情形下,把塞尔作为一个范例哲学家的不雅观点拿来当做自己的不雅观点,是不是有点偏颇了呢?
西尔
除了归纳不完备性的问题,Nick师长西席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真的理解他所批评的哲学家们的事情吗?就拿普特南来说吧,他实在是个很精良的数学家,他的层次剖析法研究在一样平常打算理论的文献中都有提及,打算机文献中提到的“Davis-Putnam算法”也凝聚了普特南的心血(后来这个算法蜕变成了DPLL算法)。诚然,普特南晚年对人工智能表现出了一些敌意,但他早期对“多重可实现性”观点的研究,实在为强人工智能话题的话语框架供应了基本的表达手段。在Nick的描述中,普特南作为人工智能同好者的一壁基本被抹去了,只剩下一个愚蠢的、卡通般的科学门外汉形象。
普特南
更多的误解涌如今作者对德雷福斯思想的描述上。作者彷佛对德国哲学的真正思想背景——海德格尔哲学——十分不屑,认为这种哲学没有算法阐明支撑,纯粹是卖强力药丸和狗皮膏药的人的胡言乱语。说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是百分百反对尼克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驳。作为一名英美剖析哲学的研究者,我有时也会为海德格尔的表述办法而抓狂。但与尼克师长西席不同,我并不疑惑海德格尔哲学至少说了一些非常主要的话,只管我并不完备赞许“海德格尔圈子”的主流如何将这些见地阐述得更清楚。 笔者的积极意见是,只要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能够被更清晰地“翻译”,他的洞见就会更随意马虎被实证科学领域事情者所接管。
——那么,这种“翻译”该怎么做呢?粗略地说,海德格尔征象学的一个基本不雅观点是,西方哲学传统关心的是“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而他的新哲学要重新揭示这种被遗忘的“存在”。我承认这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术语”,不阐明确实让人看不懂。但从事理上讲,它们也不是无法阐明的。下面我试着用普通的汉语来阐明一下。
所谓“存在”,是措辞表征中能够被明确客不雅观化的东西。比如命题、真值、主语、客体都是这样的存在。但“存在”本身却很难在措辞表征中被明确客不雅观化,比如你利用比喻时所依赖的模糊背景知识。你能否把开玩笑时的背景知识说得像你能列出十个手指头那么清楚?你能找出背景知识和非背景知识的明确界线吗?这便是传统AI的弊端。真正的人类智能活动依赖于这种不明确的背景知识,程序员不把事情说清楚就写不出程序。这构成了人类征象学履历与机器写作的机器预设之间的巨大张力。
有人可能会说:机器为什么要关心人类的征象学履历?人工智能不是克隆,以是可以完备忽略人类如何感知天下?对付这个很肤浅的问题,下面的回答就足够了:我们为什么要打造人工智能?不便是给人类加个帮手吗?假设你须要打造一个会移动的机器人帮你移动,那你难道不肯望它听懂你的命令吗?——比如下面的命令:“喂,机器人阿杰,你把那个东西搬过来,然后去那边拿另一个东西。”——显然,这个命令包含了大量的方向代词,其详细含义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确定。在这种情形下,你怎么能不指望机器人和你共享同样的语境感知呢?你怎么能容忍你的机器人是另一个时空尺度上的怪物呢? 既然这样的机器人必须具备与人类相似的情境意识,那么海德格尔哲学所揭示的人类征象学履历的一些基本构造,在某种意义上,不也适用于真正的人工智能实体吗?
海德格尔
有人可能会问:那么如何才能找到一个算法构造来实现海德格尔哲学的上述洞见呢?比如,如何在算法层面刻画“存在的可能构造”?如果不能给出一个算法构造,那不是只是在摧残浪费蹂躏韶光吗?但请大家想清楚,这个哀求该当向人工智能提出,而不是向哲学家提出。或者换一种说法:海德格尔的哲学洞见可以说是人类用户对付人工智能的“用户期望”的浓缩,而实现这些期望的重担该当放在人工智能事情者的肩上。这就好比说,如果军方哀求飞机研制单位制造一架隐形战机,那么如何设计这架飞机的任务该当是研制单位的任务,而不是军方。 换言之:你不能由于用户不懂技能细节就责怪他们没有资格提出“用户需求”,就像你不能由于军方代表不懂飞机设计的某些细节就责怪他们没有资格为军用飞机写设计标书一样。因此,如果我们像尼克师长西席一样,仅仅由于海德格尔主义者没有算法支持就将他们打倒,那么我们完备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来终结环球消费者权柄组织——消费者对技能细节理解多少?而正是由于这种“归谬法”推理的结论是荒谬的,我们可以推断尼克师长西席是把本该放在人工智能研究职员肩上的任务推到哲学家身上,从而转嫁任务,错怪年夜大好人。
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批驳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人工智能哲学家纵然主不雅观上不想关注哲学,但客不雅观上总会不自觉地预设一定的哲学态度——而正是由于他们缺少哲学鉴赏能力,他们不自觉地采纳的哲学态度每每非常低端。比如,明斯基的框架研究的基本思想是胡塞尔很早以前就遗留下来的,也早就受到胡塞尔的弟子海德格尔的批驳。但尼克师长西席不同意这种评论。在他看来,哲学家是自恋者,认为别人的思想都源于自己。换言之,明斯基的思想可以完备独立于胡塞尔的框架之外,在这种语境中完备没有必要提起胡塞尔的名字。
我认为,尼克师长西席对哲学家的不雅观点理解上陷入了严重的误解。德雷福斯当然不是解释斯基由于读过胡塞尔才设计了他的框架。而是说某种缺点不雅观念在西方思想界广泛流传,以至于哲学家和工程师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它的影响,尽监工程师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哲学家们有类似的想法。而正是由于哲学家们更简洁、更系统地表达了类似的缺点不雅观念,以是在哲学层面上谈论这个问题才能把问题阐明得透彻。
胡塞尔
当然,我对德雷福斯的支持是有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比他更激进。我赞许他对所谓符号人工智能的批评,但无法接管他对神经网络技能的激情亲切。更确切地说,神经网络无法灵巧地在不同的问题领域之间切换(比如,一个会下围棋的系统不能直接用来处理股票),也无法有效地处理句法天生的灵巧性和创造性(由于纯统计无法预测新的意义组合)——认知科学家泽农·皮利辛和刚去世的哲学家杰里·福多早在 1988 年就批评了这个问题(尼克师长西席在整本书中险些没有提到福多这位著名的认知科学哲学家)。换句话说,纵然我个人在笔墨上承认“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这一术语的可行性,但我对这一基准高度的估计比德雷福斯更悲观。
福多尔
抛开尼克师长西席对德雷福斯的误解不谈,他对其他一些重量级哲学家,比如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误解也令人吃惊。比如,他认为特里·维诺格拉德的《方块天下》靠近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措辞哲学。这实在是一个会让任何对剖析哲学史稍有理解的人发笑的结论。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朋友圈”都是奥斯汀和施特劳斯日常措辞学派的成员,他们最喜好做的便是把干净的句法剖析拉回到充满混乱和沼泽的日常语用学的地面上,他们对任何公理思想都表现出极大的疏离。考虑到《方块天下》程序背后光鲜的公理色彩,把这种方法看作是维特根斯坦早期《逻辑哲学论》的类比或许更为可靠。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虽然对维特根斯坦平生的一些八卦可能并不陌生,但他肯定没有读过《哲学研究》,更肯定没有读过我自己写的《心灵、措辞与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与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公民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心灵、措辞与机器:维特根斯坦哲学与人工智能科学的对话
说了这么多Nick师长西席对哲学的误解,我还想说一下他对认知科学的忽略,以免让人以为我太“哲学自我中央”。实在认知科学在西方出身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之后不久,1956年实在是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的“孪生年”。但纵不雅观整本书,Nick师长西席彷佛很少提到认知科学。比如人工智能的奠基人H. Simon的“有限理性”研究,实在是横跨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和经济学的三重含义,否则他也不会成为图灵奖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双料得主。但作者彷佛对Simon在这方面的事情漠不关心(经济学家们把稳了!
Nick师长西席不仅鄙视我们哲学家,也看不起你们)。幸好我并不像Nick谢绝哲学那样谢绝认知科学和经济学。 想要理解类似思想背景的读者建议阅读我撰写的干系科普读物《认知偏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
认知偏差
而且,正是由于Nick师长西席短缺对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科学之间关系的磋商,他的整本书的构造显得非常散乱。他对机器定理证明的重视,抢走了他谈论其他主要主题的空间,比如贝叶斯网络(贝叶斯网络的发明者、图灵奖得主Judea Pearl的事情也被忽略了)。而他对神经网络技能的谈论,也忽略了深度学习技能在这个方向的最新发展(比如他在谈论“AlphaGo”时,只是大略提到了一些干系技能,而没有很好地先容深度学习专家Geoffrey Hinton的事情)。至于他对打算理论的根本知识——图灵机的先容,则被放在了第10章。这就好比日本老师在第一课请教日语中最难的敬语,然后等到第十课才教最基本的50个音。当然,这本书也有独到的贡献。 比如书中第四章先容日本第五代打算机操持时表露的一些细节,在一样平常的中文书本中是找不到的,如果书中其他章节的编排也如此合理该有多好!
末了,笔者想做两点延伸评论。第一,哲学当然与人工智能有关,只管事实上有能力谈论人工智能话题的哲学家并不多。但两者的关联首先是一个规范命题,而非事实命题,后者无法推出前者——比如,如果你从“晚清中国很少有外语人才”这个点出发,就无法推出“晚清中国不须要外语人才”。同样的道理,笔者利用维基百科的文献统计体系得出的“现有的哲学文献与人工智能文献关联不大”的结论,也无法推出“人工智能不须要哲学家来插话”的结论。
第二,如果读者真的想比较系统地理解人工智能与认知科学互动的历史,还是要读认知科学哲学家写的书的,由于认知科学哲学家是跨哲学和认知科学培养出来的,更随意马虎免受狭隘学术偏见的影响。而关于这方面的书本,除了我厚颜无耻地推举我的书《心智、措辞和机器》外,还要推举英国资深认知科学哲学家玛格丽特·博登的名著《心智作为机器:认知科学史》,这也是一本必读之作(可惜这本书没有中文版,顺便说一句,这本书的作者拥有打算机科学、医学和哲学等多学科背景,与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许多大咖都有私人关系,是大咖中的大咖)。 如果读者能将博登夫人的书与尼克的书作一比较,恐怕急速就能看出“歼-20”与“歼-7”的质量差别。然而尼克师长西席的书中却没有提到博登夫人的这本长达1631页的著作。
心智作为机器:认知科学的历史
作者坦言,作者“让哲学参与人工智能”的不雅观点并非中国当下舆论圈的主流声音。在人工智能话题上,中国主流舆论圈的声音大概是受到成本力量的使令,成本界对利益回报的急迫期待与哲学家们屡屡考虑的“慢条斯理”的干事作风之间始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但或许也正是由于如此,作者以为哲学家们更有必要发声。所有逆风而行者的决心,都来自于对风向会变的信心。作者并不缺少这种信心。
徐英进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2018年天下哲学大会“人工智能哲学”分论坛中方主席
·结尾·
本文首发于澎湃新闻·上海书评,请下载澎湃新闻APP订阅,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可访问上海书评首页(shrb.thepaper.cn)。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