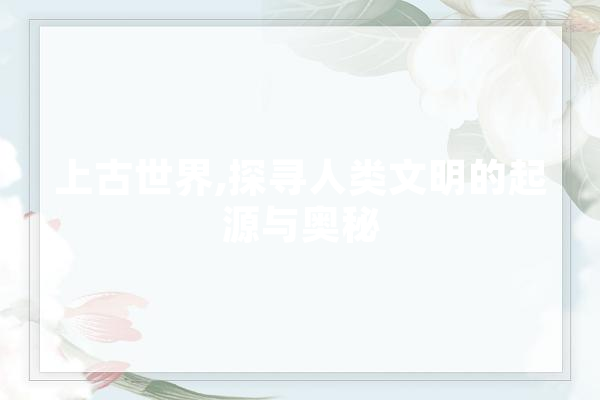是产品而非艺术品 也论人工智能与文学艺术_人工智能_人类
●未完成主体性的人工智能所天生的所谓“履历”,无法达成霎时的“浪漫”。它的产品是不会超越墨客的作品的。人工智能的算法还只是模拟,而这种模拟仍旧寄托于人类的主体性创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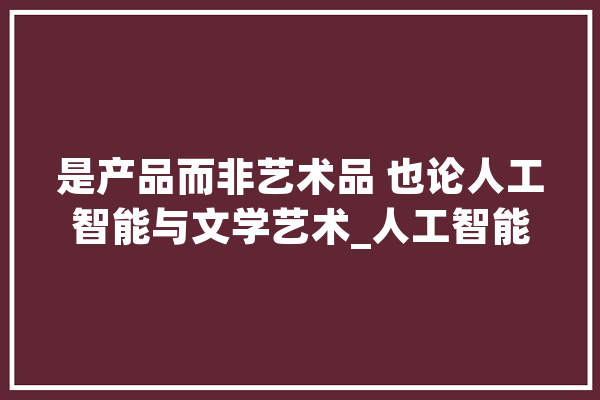
●人工智能不是墨客和艺术家,但在它的帮忙下,墨客和艺术家的潜能将被极大引发,这是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
1月15日,光明日报《文艺评论周刊·文学》就人工智能与文学艺术的关系这个话题,刊发一组文章,即《主体还是工具——人工智能与文学艺术》《人工智能写的诗,算不算“作品”——关于人工智能的“创作资格”问题》《人工智能写作是一壁镜子——由机器人小封诗集〈万物都相爱〉说开去》。三位作者从各自的角度,阐述了人工智能对付文学创作的潜在影响,并对未来的更多可能性进行预测和评估,读来让人受益匪浅,有话想说。
的确,人工智能已开始参与到诗歌、散文等文艺创作之中,乃至天生的某些产品具有特定的风格,有“类人”的趋势。随着智能媒介技能的快速发展及5G时期来临,人工智能业已渗透到人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当来世界的同时,也为文学艺术创作带来了新的命题。它的运用正改变着审美客体,解构着审美主体,其间也伴生出诸多审美问题。
人工智能之于文学艺术,只是一种技能手段
技能与艺术的关系是一个古老命题。技能的进步,可以为审美实践供应更多的元素。人工智能虽然有可能改变文学艺术的生产办法,乃至改变艺术作品的范式,但它所天生的只是产品,并非真正的艺术作品。在艺术起源的早期,技能与艺术并没有什么差异,古希腊人把凡是可以通过知识学会的事情都视为艺术,对艺术和技艺、技巧不进行区分。但是,艺术与技能是不同的。艺术创作具有更强的非预期性和无规定性,属于“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人类纯逻辑的能力可以编码,但一些超越逻辑的能力,如直觉反应、灵感不可编码,数据不能等同于知识,算法不能大略地与创作画等号。
弱人工智能在措辞、感性和创造力层面,存在着显著困难。对付这些人类所独占的文学艺术创作层面的范例特质,弱人工智能目前只能做到一定程度的仿照。在措辞层面,人类日常利用的措辞是人类自然措辞,由人类社会发展演化而来。概括来说,自然措辞是人类社谈判定俗成的,差异于如程序设计的措辞,也便是人工措辞。多数的人工智能运用程序利用“自然措辞处理”(NLP),关涉的是打算机对呈现给它的措辞的“理解”,而不是打算机自己创造措辞。因此,对“自然措辞处理”而言,创造比吸收更困难,包括主题内容和语法形式。在语法上,人工智能天生的诗歌常日很不恰当,乃至有时是禁绝确的。人工智能的诗歌产品,虽然形式上有先锋派的痕迹、后当代的味道,或许能给予读者一种“震荡”的短暂体验,但由于没有历史深度和韶光刻度,显然属于一次性过的“仿后当代”。诗歌不能缺失落历史的灵魂,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历史没有诗歌是了无生气的,而诗歌没有历史则是乏味的”。
基于感情和情绪依赖于人类大脑中散布的神经调节这一事实,“感性”也是人工智能难以企及的能力。虽然日本软银公司开拓出“云端情绪引擎”机器人“派博”(Pepper),试图仿照神经调节,但效果并不理想。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运用层面,大部分研究仍很浅表。而感性是艺术创作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品质。
在创造力层面,文学艺术创作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这一主体性的特质也是弱人工智能所不具备的。至于强人工智能何时拥有主体性的创造力,未来并不可期。英国认知科学家玛格丽特·博登将创造力分为组合型、探索型、变革型。她认为只有探索型才有可能适宜强人工智能。然而,纵然是探索型人工智能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人类的判断,由于只有人类才能识别并清楚地解释风格化的法则。倘若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剖析文学艺术的风格,那么,这种创造性探索才能被称为创作。事实上,目前人工智能的智能模式远不如人类,实质上仍是人类的工具,是一种技能手段。
在完成自身主体性之前,人工智能很难剥夺人类的创作权
真理即创造原则,是18世纪早期哲学家维柯所强调的。只有人类大脑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创造物。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也笃信,人类的创造力即自我诠释,是一种前逻辑的思维能力。人类在自我认知系统与自然天下的交互之中,理解了自我和天下的关系。当反思自我时,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大脑可以不雅观察自身,二元对立就消逝了。自反性乃是人类最紧张的主体性。这种特定的自我,可以让无意义的元素呈现出意义,这也是艺术创作产生的本源之一。目前人工智能并不能实现自反性。斯坦福大学研究职员演习机器人乘坐电梯,机器人会在门前停下。它把电梯玻璃门里的影子当成另一个机器人,并不能识别一个被放大的自己的影子。
文艺创作是超验、反思和自洽的,既包括方案构思过程,又包含构造、节奏活动。它以不雅观念的构思形成艺术的表象,并以此作为生产的条件,从而使创作活动依据人的自觉目的进行。作品包含了主体对文化的整合和想象的跳跃,有物质层面的,有行为层面的,更有精神层面的,既具有技能属性,更具备创造属性。人工智能的诗歌产品,目前只具有创造属性中的转换创新,实质上还是通过“人—机”帮忙、协同的办法完成的。
对付人工智能而言,算法是大脑,算力是肌体,大数据是其发展的养分。基于深度学习的机制的人工智能,并不理解自己所天生产品的意义。它所做的只是在算法的驱动下,将一种形式投射到其余一种形式上。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是比“算法”繁芜得多的精神活动。
人工智能并不面向文学艺术,深度学习机制丝毫不关心读者是否会欣赏其产品。所谓的人工智能诗歌,是一种浅表的类型化文本,不能让读者实现永恒崇高的神圣性审美体验,只能知足读者的好奇心。
人工智能在文学艺术创作中可以成为墨客或者作家的助手,但不可能替代墨客或者作家。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的非创造性重复事情,可以由人工智能承担,但是创作主体的心灵天下,墨客和艺术家的感性思维能力,艺术创作主体的灵感顿悟能力,是人工智能不可得到的。在完成自身的主体性之前,人工智能很难剥夺人类的创作权。未完成主体性的人工智能所天生的所谓“履历”,无法达成霎时的“浪漫”。它的产品是不会超越墨客的作品的。人工智能的算法还只是模拟,而这种模拟仍旧寄托于人类的主体性创造。
在人工智能帮忙下,人类将引发出更多的艺术潜能
我们也应看到,在反人类中央主义的框架中,在后当代的视域下,人工智能的进化是否可以承载些许“诗性”,还不能妄下定论。人类的身体、大脑等与生俱来的构造,决定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认知局限。人脑的局限性使人类无法理解一些终极真理,人类可知晓的事物范围存在边界和上限,以是我们应避免把人工智能狭隘化。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对技能持乐不雅观态度,他不但怀念机器复制时期之前的“灵韵”,也为技能变革所带来的艺术新形式欢呼。他所定义的机器复制文明时期已发展到人工智能时期,人工智能不再是大略的机器复制,而审美客体并未因之面孔全非。在后当代主义看来,原创性不是判断艺术作品的最高标准,艺术哲学的美的观点性过于沉重,固执的理性不雅观念主宰着审美,艺术必须冲破这种界定。艺术与非艺术、反艺术之间的区分是可疑的,艺术本应多元、异质。
文学艺术属于一种“家族相似”,是相似性之网,它的观点该当开放和洞开。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文学艺术可能会更加多元。而多元性谢绝虚假的抚慰,它的目的是使艺术通向真理。
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人类的生活办法、生产办法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艺术与人工智能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领悟,将引发人类无限创造的潜能,新的艺术范式将产生,艺术创作也将前所未有地变得更加日常。人工智能不是墨客和艺术家,但在它的帮忙下,墨客和艺术家的潜能将被极大引发,这是一道令人神往的风景。
(作者:朱志勇,系黑龙江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案项目“领悟媒体时期生活审美化研究”阶段性成果)
来源:光明日报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