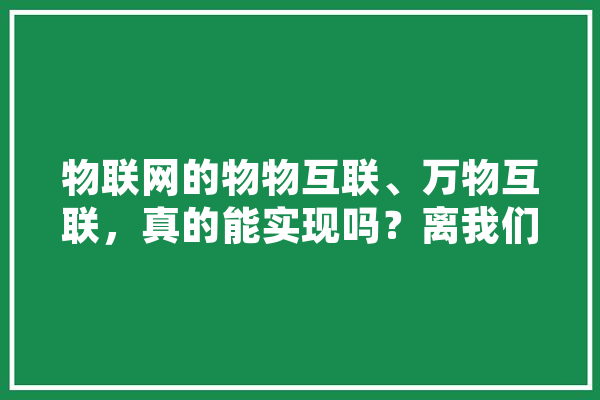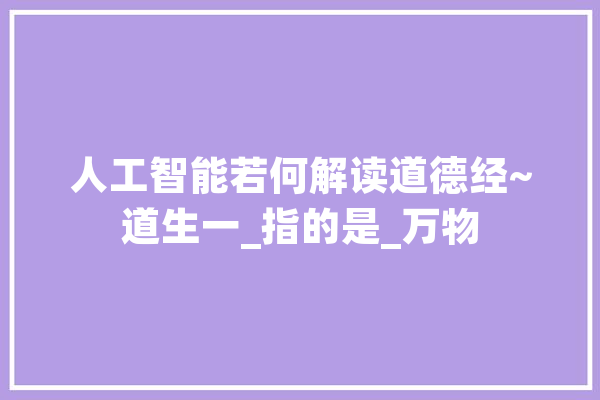“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是一回事吗?_天人_董仲舒
文/清虚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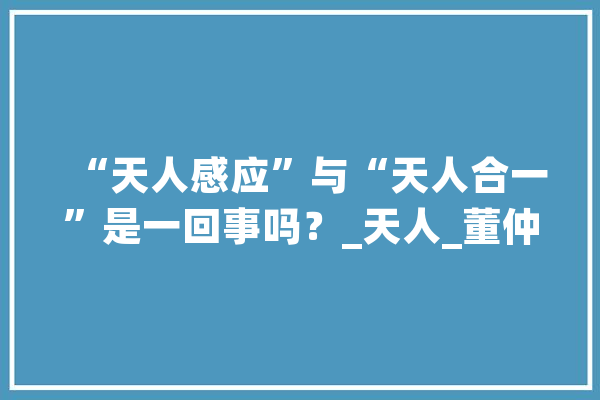
在中国人的传统崇奉中,敬天是一项很主要的内容。天人之间的关系,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人在做天在看”,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老天爷彷佛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在封建王权社会,身处皇位的“天子”的称号以及“替天行道”的叛逆旗号历代更迭不断。在对天的崇奉的支配下,“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是最常被提起的两个观点。天人感应,代表的是早期儒家所倡导的谶纬神学;天人合一,代表的是早期玄门所提倡的宇宙哲学。这二者不但不是一回事,其在所追求的终极命题上还有着实质差别。
“天人感应”一词源出于《尚书·洪范》,其写道:“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晰,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意思是说,当朝君主的施政态度如何,会影响到大自然的景象变革,认为人的行动实在是与天象有关联的。孔子在作《春秋》的时候,也曾经提出“邦大旱,毋乃失落诸刑与德乎”的疑问,并规劝国君要“正刑与德,以事上天。”由此可见,早在先秦期间,天就已经被人们供奉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具备根据人类行为的善恶而做出征兆的主动性。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便是这一不雅观点的集中表示,而孔子强调的“开罪于天,无所祷也”则直接奠定了人类在苍天面前的无能为力。
在此根本上,作为“天人感应”论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在进谏汉武帝的时候说:“国家将有失落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磨难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其不雅观点基本上继续了先秦期间的“灾异说”,同时董仲舒还充分发挥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天生论,认为天地与人类自身的祸福、社会秩序的制订都是按照五行的生克来运转生存的。
当万物合于五行,则生生不息而万物昌;若万物背离于五行,则天降灾异、社会失落序、万物皆祸。董仲舒还认为,构成天地万物与人类自我的基本物质是相通的,他秉持“气化论”,主见人之气若能够调和顺适,天地之气因感而一定化现祥瑞。相反,人之气如果邪乱乖谬,当此气与天地之气相稠浊时,就会使得灾象丛生。“世治而民和,志平而气正,则天地之化精而万物之美起;世乱而民乖,志癖而气逆,则天地之化伤,气生磨难起”,这是“天人感应”论的一项主要内容。
在灾异遣告说与天人同类说的根本上,董仲舒更进一步神化了天的存在,他提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的主见,把天认定为宇宙间最至高无上的主宰。不论是自然界的万物生化,还是人类社会中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都是天神按照阳贵阴贱的意志来安排的。人们的行为如果符合天意,就会得到上天的褒奖;如果不符合,就会受到上天的制裁。至此,天人感应的思想基本形成。这一套具备神学根本的天下不雅观,不仅为当朝统治者供应了一统天下的君权神授理论,更成为中国式宗教神学出身的根本。
只管董仲舒及其带有儒家纲常色彩的“天人感应”论是建立在先秦道家及阴阳家“天人合一”理论根本上形成的,但很显然其把先贤口中“天”的观点狭隘化了。
天的意象,有三个不同层面的表达:一为自然之天;二为董仲舒所谓之天神;三是对人类社会及自然界运行秩序的某种概括性表达,此略同于老子讲的“道”。
《庄子·达生篇》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道家讲到的天之父母与人之子孙之间并非是自然的生养,而是对生化征象的形象性表达。“大道无情,生养天地”,这种“生养”是自然万物按照固有的规律和准则长期蜕变的结果,并不是秉持了某位神明的意志,也不会由于规则的演进或改变而遭受惩罚。正相反,万物法自然,天有天之自然,人有人之自然,这种自然是“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故道大,天算夜,地大,人亦大。域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道的层面上来看,天与人是可以并称的。
此不雅观点乃至可以追溯到《易经》中,其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阴阳、柔刚、仁义,皆是自然之道在不同方面的不同表示,三者本于一源,彼此之间是同与应的关系,又何来尊卑之差别?”
《黄帝内经》中反复强调一个不雅观点,曰“与天地相应,与四季相副,人参天地”,其认为人的生理和精神意识都该当参照自然规律的运作,以此思想来调和身心才能实现炼养的目标。在崇尚自然的道家学说中,天人合一是修真的最高境界,表示出来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而非从属关系。
季羡林先生长西席说:“‘天人合一’便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强调人类的行为要合天道,否则就会自遗其咎,但这种合道的思想、行为并不因此某种附加了人格意识的神明做主宰的,而因此天地万物都须要遵照的自然之道为准则。自然,乃是自我之本然,是每个事物自身所具有的规律。以是在道的支配下,万物只管表现出千万种不同情态,却又都遵照同一个内在法则。天人合一,追求的是万物在道的层面上的同一,即是和谐共生。
庄子言:“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正好是由于人类社会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来限定自然本性,才阻碍了自我对道的体认。以是老子极力倡导“绝圣弃智”,把“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各种规章制度打碎,真正解放了人性,才能使人们复归于自然,终极实现“万物与我为一”的超越境界。
比较起“天人感应”的思想,“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家之思想,更是万物的对生存状态的表述。其二者于不同处的比较,正好印和了儒道两家秉持的不同天下不雅观。中国历史上,儒道思想以阴阳之态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基石。虽然源头和主见不尽相同,但经由历史的演化后,“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两种思想逐渐相互接管,在百姓的崇奉中已经无太多二致,这大概也正是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兼收并蓄之原谅性的范例表现之一。大儒程颢的“天人本无二,不必有合”的不雅观点,便是对“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两种思想的最好总结。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