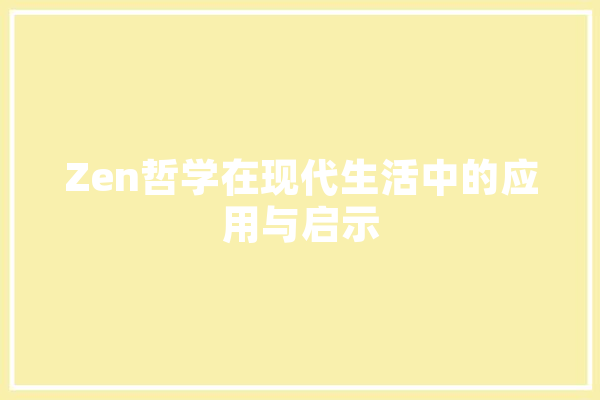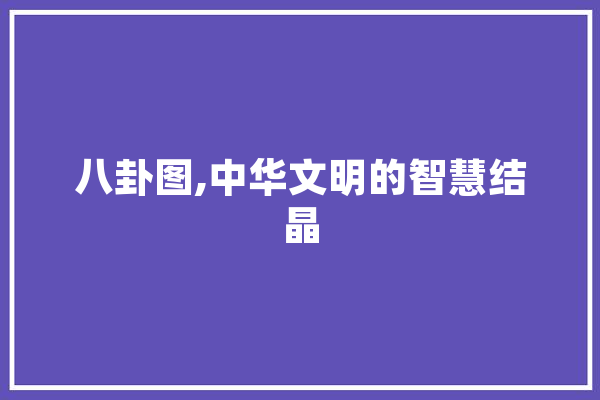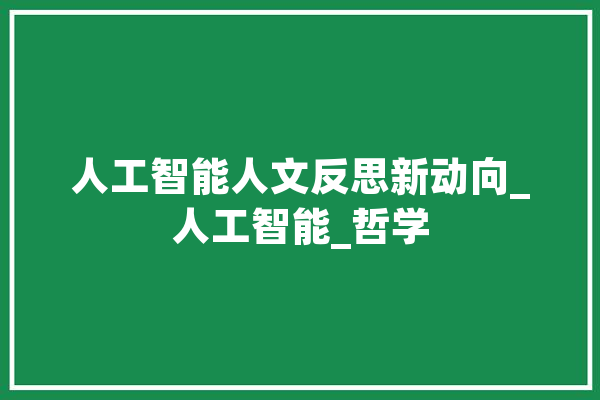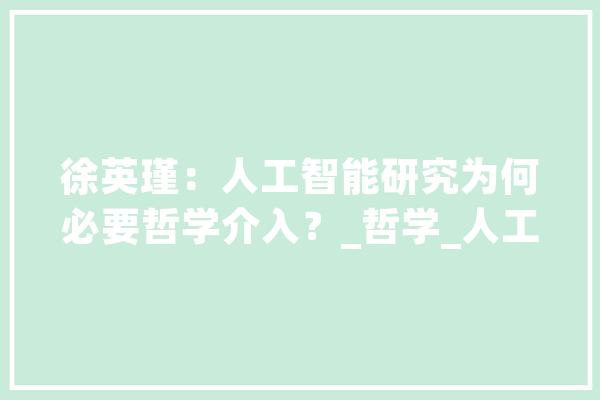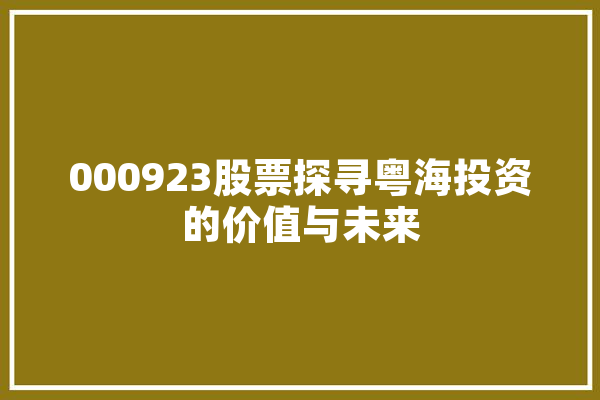人生意义何处寻?人工智能是仇敌?大年夜咖解答你最关注的哲学问题_哲学_美妙生涯
光明日报评论部约请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位哲学教授,在世哲会间隙,为网友解答个中部分问题。读罢四位学者文章,你会惊叹于哲学居然离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么近,这么夷易,这么有趣。
华东师范大学欧陆政治哲学研究所教授吴冠军向日常生活发动“打击”的哲学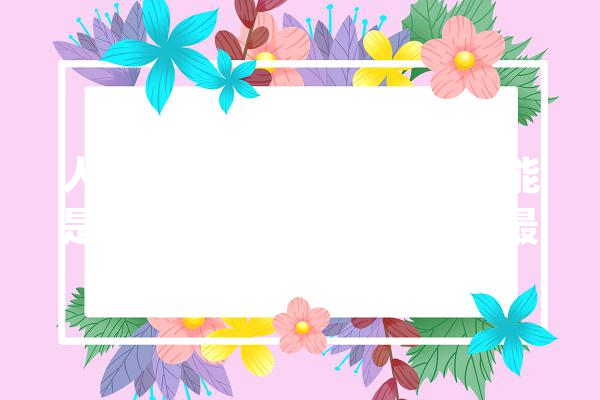
哲学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它们有没有关系),从来是人们最想理解的。那是由于,哲学一贯给人一种在“云端”上的觉得,跟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对付很多人,那些大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等,一是读不懂,二是也不必读——没有同哲学发生关系,觉得并不影响自己当下的生活;而读了哲学,觉得也没什么特殊帮助。乃至不少专业搞哲学研究的学者,觉得也便是作为换取薪水的事情在“搞”,跟他自己生活也没啥关系……这,实在是经由经院化和学科化的“哲学”,对哲学原来面貌的最大扭曲。
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视哲学为一种生活形态(lifestyle),哲学就在人们的逐日相遇中、对话中、彼此提问和谈论中,尤其是对那些人们视作为知识的内容重新提出追问。苏格拉底本人就常常向城邦中的公民追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崇高”、什么是“节制”、什么是“猖獗”、什么是“年夜胆”、什么是“懦弱”、什么是“根基”、什么是“城邦”、什么是“政治家”、什么是“统治”……所有这些词,都是当时人(包括今人)每天在用、却并没有真正寻思过的观点。作为生活形态的哲学实践,便正是把日常生活中那些被反复利用的词,变成观点(哲学观点),在各种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问题(哲学问题)。这,便是“哲学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世编年夜哲海德格尔把苏格拉底称作为“西方最纯粹的思想家”。换句话说,苏氏以降,“专业”的哲学家越来越多,但哲学却越来越不“纯粹”,终极变成一门“专学”,而不再是一种生活形态。于是海德格尔竭力重申:哲学是对人类总体方方面面的一个打击,从“日常性”开始探寻,趋向事物的根基。日常性,是哲学的出发点,我们必须从那里出发。那是由于,对付我们每个人(海氏称之为“此在”)来说,日常性是无可躲避的,是“最紧张的”、“最大部分的”。并且,正由于它是如此靠近于我们、如此熟习,它常常被忽略。海德格尔写道:“生活中最靠近、最熟习的东西,便正是存在论上最迢遥的东西,我们对它的存在论意义是无所知晓的、惯常忽略的。”通过“此在”这个著名观点,海德格尔要把哲学重新拉回到日常生活中确当下情境,拉回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
海德格尔完备点出了哲学的原貌。哲学必须刺入日常生活、打击日常生活,在那里提出问题,并走向根基。而深受海氏影响的过去大半个世纪的欧陆哲学,大规模地打破了传统“哲学”的学科壁垒,以“游牧”、“去领土化”(德勒兹)、“越界”(巴塔耶、福柯)、“解构”(德里达)等办法展开哲学研究。在最近半个多世纪的欧洲大陆,大哲学家呈井喷式呈现,呈现一派群星残酷的盛景,并且,这些大哲们很多都同时兼具很多“学科”身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宗传授教化家或神学家、精神剖析师、政治学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传播学者、思想史学者、文学批评家、艺术批评家、文化研究以及电影研究学者、乃至直接便是文学家、艺术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有人乃至是总统候选人,差点就当上了国家元首……这些大哲不单打开了各种“学科”各自封闭性的边陲,实在,首先打开了传统哲学自己的封闭性边陲,把许多原来哲学不管不顾的问题,纳入进了哲学剖析的视域中。他们把哲学从原来一门早已专学化、经院化的专门学科,重新变成联结各种思想实践的网络中央。
故此,存在着两种关于哲学的治学办法:一种是从生活天下人之群处的详细问题出发、从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日常性”出发、从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存在性焦灼出发展开思考;另一种则是从“哲学”学科内某一组抽象的观点、术语或成说出发,通过对它们的讲明与阐释来谈论问题。而哲学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重新在欧洲大陆复兴,正是由于出来一批传统哲学眼中的怪咖式哲学家——他们一反学科性的治学办法,谢绝在传统哲学框架中顺着讲、在“云端”按着既定轨道往前走;他们相应海德格尔的号召,激烈地、欠妥协地冲出了经院哲学的束缚,冲到日常生活的地面,在那里展开游牧式思考、游牧式打击。在本日,哲学家乃至可以出“笑话集”这样的书,跟你讲讲你为什么会笑倒在那些段子之下……
你的日常生活更加明艳动人,当哲学闪耀时。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人工智能,人正在创造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大约进入21世纪往后,哲学家才不可避免地面对科学技能的寻衅。此前,马克思与恩格斯那一代哲学家还大多惊叹于科学技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将技能看作是人延长了的手臂,直到20世纪往后,两次天下大战催生出了技能的军事化用场,让诸如海德格尔这一代先贤大哲创造了技能与人之存在之间的内在悖论,直到20世纪中晚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目前仍旧在世的哲学家哈贝马斯曾将“科学技能即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哲学命题进行论证,他的试图解释的是技能成为了与成本发展共进退的共谋者。时至今日,技能早已不再是社会发展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了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出一个强大的仇敌。
技能对付人类的这一严厉寻衅很随意马虎让我们想起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曾经为自己设计的一个悖论性的难题:上帝能否创造出一个自己都举不起来的石头?不管我们的答案是什么,终极都会将上帝推入到与其“全知全能”之属性相悖谬的田地。当时的经院哲学家们对这一悖论辩论不休,而这一辩论终极推动的只是一种空泛的思辨哲学的逻辑推演,但本日这一逻辑推演的悖论性却极为真实的困扰着人类生存本身。自从AlphaGo与Alpha Zero相继出身,人们开始对付技能的自我增长产生了普遍的恐怖,人工智能,人的这个创造物降服人的神话正在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变为现实。
人类生存的每一次危急都须要哲学家的关注。哲学,虽然是一种爱聪慧的学问,但却根本上以关注人的生存为己任。技能,原来作为一种人类知识力量的外化形式,曾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手段。因此,当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那句尽人皆知的“我思故我在”,其所设立的不仅是哲学的第一事理,也为知识,以及科学和技能设定了第一事理。从此科学研究就可以犹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平常任意驰骋,为什么呢?缘故原由很大略,由于笛卡尔的哲学原则见告我们人(我思的主体)成为了全体天下的理论根据,人作为天下主体,人也就成为了天下的上帝。
当代社会便是人这个上帝创造出的一个人化天下,如今这个上帝正在制造一个自己搬不起来的石头,于是开始惶恐,仿佛这一境遇是人类从未遭遇过的寻衅。实在,本日人工智能对人类存在造成的危急与二战期间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惶恐并无二致。它所表达的都是技能对付人类生存构成的威胁。在哲学上,我们可以用知识论与存在论的对抗性关系来概括这一危急。技能实质上是哲学知识论的一定后果,其基本的诉求是试图将天下上存在的统统都进行形式化的抽象,也便是说,将统统都还原为抽象的数字,从而适用于可打算性。而存在论,则意味着对付人自身的关照,个中人的感情、情绪成为了关照的重心。大体说来,那些对付人工智能充满信心者,以及那些对付人工智能所产生的威胁心坎不安者都不过是知识论的拥趸;而大部分的哲学家们都可能会立足于存在论,而对付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威胁不以为然。为什么?缘故原由不难明得:人工智能能够完备替代人的玄想之以是能够成立关键在于你将如何看待人之人的属性,如果你认为人的实质便是一个可以被还原为一组组数字,如同一部巨大机器上的零部件,他的每一时候的行为都是被规定好,他的未来的每一种可能性都可以被打算出来,那么你当然会以为人可以被人工智能-人所替代。但如果你认为人生便是有时性事宜串联在一起的一场戏剧,其间上演着的每一分钟都包含非确定性,它的精彩是不可预期的,那么你根本不会相信任何一部机器可以完备替代你的存在。
人工智能在本日社会所带来的惶恐,一方面源自于成本的诉求,其故意制造话题,以便洞开新的利润增长点,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的生活越来越多地被知识论的抽象原则所操控,比如人有了身价,成为了可买卖的商品,人的事情韶光十分固定,以至于一天的生活与一个月每一天的生活毫无二致。这在哲学家看来是一种范例的非人的存在样态。人工智能所代替的,也只能是非人之人,而非人本身。
正是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产生了一个契机,它让人可以溘然越来越自省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人类活动当中究竟有多少是不可打算的部分,以便将我与机器区分开来。是的,正是人工智能,让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了“人本身”。
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王时中人买卖义何处寻?古人云:“人生识字忧患始。”意思是说,学会识文断字,固然能够给人的互换供应方便,给人的精神带来愉悦,但也可能使人“杞人忧天”、患得患失落。这也是近期“中国民众最关注的十大哲学问题调查”中,“人生的代价与意义”居榜首的缘故原由。
相对付不识字的动物不会涌现的烦恼与困惑,有了笔墨之后的人类不得不面对难以两全的困境:一方面人的自然生命注定人有生必有去世,要吃也要喝,会搔痒,会打嗝;另一方面人的文化生命又使得人不安于自然生命的知足,而总想打破固有的限定,授予生活以代价与意义,乃至不惜与人的自然须要相对立。如不食“嗟来之食”、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刚毅不拔。问题是,当人探求自身的意义时,用什么作为尺度呢?如果仍旧用人自身的尺度,那么,尺度与工具同一,怎么能够衡量呢?用人之外的事物作标准吗?但人自认为是万物之灵长,又岂肯服从他物?由于这本身就贬低了人存在的意义。
周国平师长西席因此认为,意义的寻求使人陷入二律背反。这种状况既是人的伟大之处,也是人的悲壮之处。高清海师长西席则直接区分了人的“种生命”与“类生命”,认为人同时具有这二重的生命而不会自相抵牾:种生命为人与动物所共有,有生便有去世,非人所能自主;而类生命则是由人创生的自为生命,为人所特有,是对种生命的超越,由于它能打破个体的局限,得到了永恒的、无限的性子。
正由于人具有不可通约的双重生命,因此,如何处理与折衷这种二重性关系才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任何偏执于一真个不雅观点都是不全面的:人固然须要知足自然生理须要,但也有安全的须要、被尊重的须要,更有安身立命的须要,追求永恒与不朽的须要。相对来说,后者对付人更为主要,这实在也是每个民族所珍惜的代价不雅观。而这些代价不雅观因此精神产品的形式被保存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
每个人的心智发展都离不开精神产品的滋养与润泽,特殊是文学作品中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对每个时期的人们更是产生了深远而持续的影响,人们也通过这些形象与古人保持持续的精神沟通,从而得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意义源泉。由此可见,无论古今中西,伟大的精神产品是永不过时且常读常新的,反过来说,精神产品作为不同时空的人们所相互认同的最大公约数,人们也因此而能够形成了代价共识,进而在此根本上构成了不同形式的文化共同体。
不能恰当处理这种二重性关系,正是人们陷入代价危急的根源。特殊是在物质生活得到知足之后,如果缺少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人极易变得高度自私、功利、狭隘,由此产生了对生活的迷惘、困惑,进而产生焦虑、烦闷,这些感情大大地稀释了由于物质生活的丰裕而给人带来的幸福感,人们反而有些怀念以往相对贫穷,但精神状态更为充足的时期。然而,人总是要寻求某些精神寄托的,当缺失落康健的精神产品勾引的时候,人们便毫无选择地转而探求廉价的精神替代品,于是,各种浅薄、粗糙的不雅观念形态便应运而生,且装神弄鬼,不一而足。
对一个没有宗教传统的民族而言,当原有的代价不雅观受到冲击进而损失实在际根本之后,它既要面对当代宗教世俗化大潮的裹胁,又要面对消费社会的滚滚年夜水。前者在“上帝已去世、万事皆可”的名义下,反抗神圣,消解崇高,抵制崇奉;后者则坚信钱能通神,崇尚物欲横流、醉生梦去世的所谓时尚生活。在这两种思潮夹击之下的人陷入到代价的迷失落与意义的虚无,就一点也不奇怪了。要走出这种困境,有待人文科学研究者,特殊是哲学研究者的精神生产活动。因此,如何把握与回合时期的问题,进而在代价不雅观上生产出高质量的精神产品,真正引领、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折衷人们的自然生命与代价生命、种生命与类生命的关系,是哲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思想义务。这次天下哲学大会以“学以成人”为主题,大概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吧。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或许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个体那里,会有着不同的回答。美好生活,或是在金碧辉煌的厅堂里的一餐盛宴,或是小憩之后,小啜一口咖啡,或是远眺前方的青山绿水,品味着带着芳草醇喷鼻香的空气,或是在情人的怀抱里,瞩目着对方眼神的嫣然一笑。对付一个个体,或者一个家庭来说,这样的幸福或许是美好生活的标志,不过,若是放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全天下的范围里,这样的幸福不雅观就显得有些狭仄了。在新时期的背景下,随着公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改进,也随着科学技能日月牙异的发展,我们须要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来重新思虑美好生活在本日中国的含义。
显然,当谈到什么是美好生活时,首先想到的问题便是物质生活上的富余。在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就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意味着唯有实现了物质上的富余,美好生活才具有可能性。当人们还在为衣食住行而困顿时,很难说人们是幸福的,管仲的策略便是通过实现物质的富余,为齐国赢得太平。在马斯洛的须要层次理论中,也是将物质层面的生存须要,算作人们须要知足层次的最根本的条件。以是,只管不能大略地将美好生活即是物质生活的富余,但是,倘若没有物质上的基本知足,公民的美好生活便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培植取得了巨大造诣,公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巨大改进,这无疑为创造和培植美好生活奠定了良好的物质根本。
不过,仅仅有物质上的富余,不敷以实现真正的美好生活。正如此多葛学派的哲人塞涅卡所说:“我们有必要重视一下我们生活幸福的外部条件——物质财富,但是千万不要对其付出过多的爱,由于你是财富的主人,不是财富的奴隶”。无论是古希腊罗马的哲人,还是中国先秦的圣贤,都不会将物质上的知足视为幸福。相对付身体上的知足,相对付生活条件的改进,这些古代的先贤,更看重的精神上的伟大和宁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物质条件,相反会成为阻碍他们得到精神上的美好生活的障碍。犬儒学派是一个最极度的类型,当第欧根尼住在他的木桶里的时候,代表着他们对物质财富最极度的谢绝办法,相反,他将精神上思虑视为通向幸福的条件。当然,我们并不须要本日都像第欧根尼那样,在木桶中实现精神上的美好生活。但是,我们须要理解,在那些思想家那里,美好生活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升华,他们将聪慧、年夜胆、节制、谨严等作为美德,在美德的不雅观念上生活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同样,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周敦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成为中国士大夫们对高风亮节的生活办法的推崇,而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已经成为中国文人美好生活的一个榜样。
当然,美好生活既不是勾留在最根本的身体和物欲的知足上,也不一定要向颜回、周敦颐、塞涅卡、第欧根尼一样,安贫乐道,知足于抽象的精神追求。我们须要理解的是,美好生活,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美好生活。我们一旦提出了美好生活的观点,就该当将其放置在更广阔的视野之中。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的时候,我们该当明白,美好生活,首先该当有兼济天下的肚量胸襟,仅知足于自己物欲固然陋鄙,但仅仅追求自己的精神天下,亦不是理解美好生活的好的办法。我们始终处于一个共同体当中,唯有这个共同体能够彼此平等和谐,能够达到普遍的正义,美好生活才是可期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肚量胸襟,换言之,真正的美好生活,只能建立在一个更为公道和平等的共同体根本上,而不可能勾留在堆金积玉的物质条件之上,也不可能是曲高和寡的文人墨客的精神追求,唯一能够实现美好生活的,只能从现实的历史背景出发,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层面上,创造一个更公正,更和谐,也更具有兼济天下精神的共同体,只管这个目标仍旧十分迢遥,但这确实是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评论部
本期编辑:刘嘉丽 常莹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