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作品?_人工智能_独创性
根据上述定义,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应该包含以下四个要素:
特定领域: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独创性有物质表现形式(可复制性)属于智力成果2.争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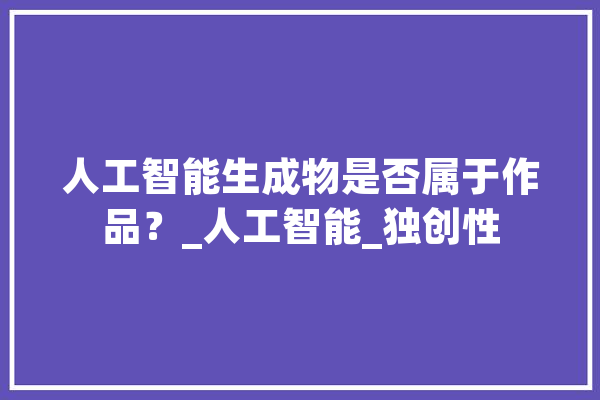
关于人工智能创作物是否属于作品,理论上存在对立不雅观点,笔者根据近几年对此议题进行谈论的文献,对干系不雅观点归纳整理如下:
不是作品:
从创作过程稽核,人工智能天生物实质上是一种模拟,只是这种模拟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的根本上变得不易觉察,其复制与模拟的能力借助于打算机技能而大为提升,成为了一种基于海量数据的分裂、重组和杂糅,和复制、模拟某一个或某几个详细作品的行为比较起来显然更难甄别和判断。这种创作过程在实质上是一种打算,根本无从知足独创性的哀求。(曹博. 人工智能天生物的智力财产属性辨析[J]. 比较法研究, 2019, (4): 138-150.)
对付人工智能天生的内容而言,即便在表现形式上与人类创作的作品几无差别,如机器人天生的人像素描和财经宣布等,由于是运用算法、规则和模板的结果,其天生过程没有给人工智能留下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空间,不具有个性特色,该内容并不符合独创性的哀求,不能构成作品。(王迁.论人工智能天生的内容在著作权法中的定性[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报),2017,35(05):148-155.)
目前,机器依赖大数据算法产生文章进而主见构成作品的案件已进入法院,这类案件实质上还是机器在运用人的智能的产物,人对机器天生物具有较强的掌握能力,从数据的网络整理输入,到写作的触发,均在自然人的设计和选择之中,其本色上仍旧是自然人智力成果的延伸表示,不过是借助更为强大的机器(算法)手段呈现出来终极的结果,且在过程中能表示出机器自身一定的“处理能力”。(杨柏勇:著作权法事理解读与审判实务,法律出版社)
是作品:
著作权法只保护独创性的表达,不保护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创作过程判断人工智能智力成果是否是作品,难免不适当。……判断“智力成果”是否是作品,著作权法只能依据展现在外的表达判断是否具有独创性,无法察知创作者的真实意图和想法,作者是如何把作品创作出来,更不是著作权法调度的范围。(李伟民. 人工智能智力成果在著作权法的精确定性——与王迁教授商榷[J]. 2021(2018-3):149-160.)
独创性中所谓“人”的创作这一理解,说到底是一个权利归属问题,它与“作品是否在表达形式上具备足够的创造性从而享有版权”,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将“人”的创作作为“独创性”的内涵,稠浊了权利客体的属性与权利归属在法律技能上的差异,毁坏了法律的基本逻辑。……版权法中的独创性判断标准,应该向一种客不雅观化判断标准倾斜,即从形式上稽核其是否与现存的作品表达不一样,并在人类自己所创设符号意义上是否能够解读出具有“最低限度的创造性”。(易继明. 人工智能创作物是作品吗?[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 2017, 35(5): 137-147.)
从以上剖析可知,独创性被用作了评判人工智能天生物是否属于著作权客体的核心标准。反对者认为,人工智能天生物的产生过程不具备独创性,故而其天生物不属于作品;支持者认为,独创性是对天生物本身的外在客不雅观评价。
3.一些想法
笔者认为,首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割裂的。当我们谈论创作或者创造时,隐含人类智力活动这一要素,因此,人类智力活动的投入对付人工智能天生物性子的判断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权利主体的问题,其对付判断独创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类智力的投入是独创性的来源,没有人类智力活动的参与的制造过程不是创作,其“制品”当然不属于创作物。因此,独创性与智力成果之间存在耦合性,即作品一定是人类智力活动所产生的成果。可以认为,在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未得到承认的情形下,人工智能天生物肯定不是人工智能本身的智力成果。纵然是法律非自然人主体著作权有所规定 ,上述论断仍旧适用。
其次,很多情形下,是否将某些客体视为作品是纯粹的技能性问题,与其问是不是,不如问需不须要。当前对人工智能天生物可版权性的谈论都是建立在若不授予其著作权客体地位,则其无法得到有效规制和利用的假设上的,但事实是人工智能天生物不被视为著作权客体并不虞味着不能作为权利客体。若条约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能够有效地保护各方的利益,则将人工智能天生物纳入著作权法中作品的范畴并非必要。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