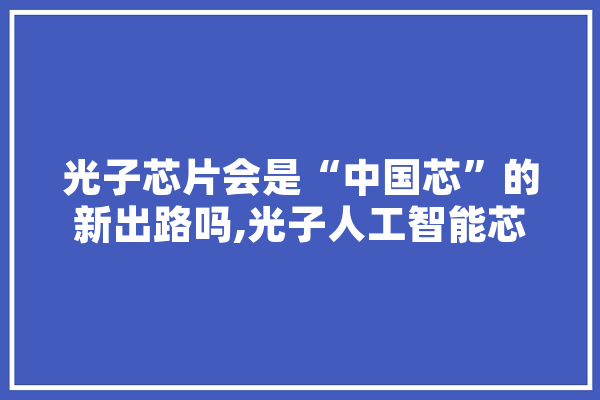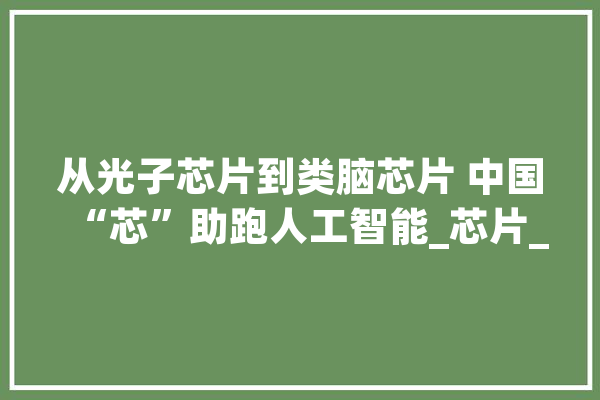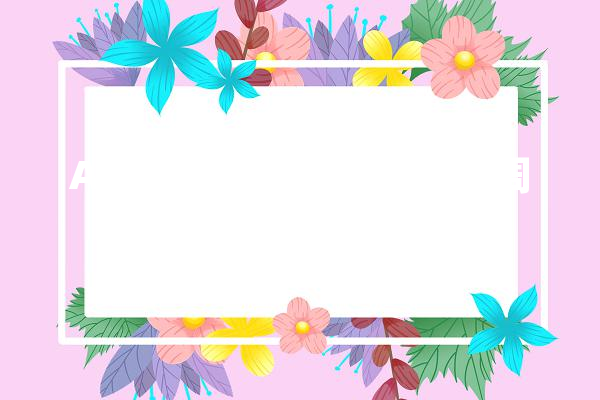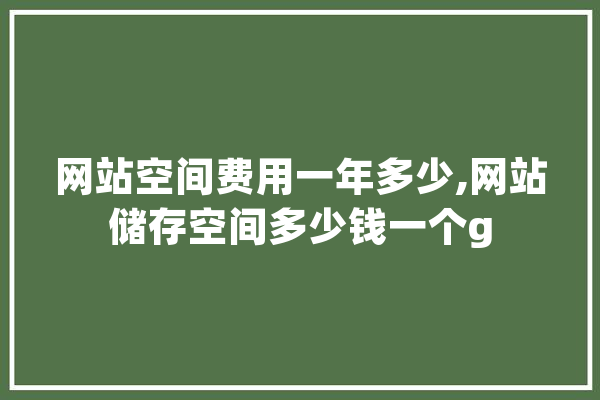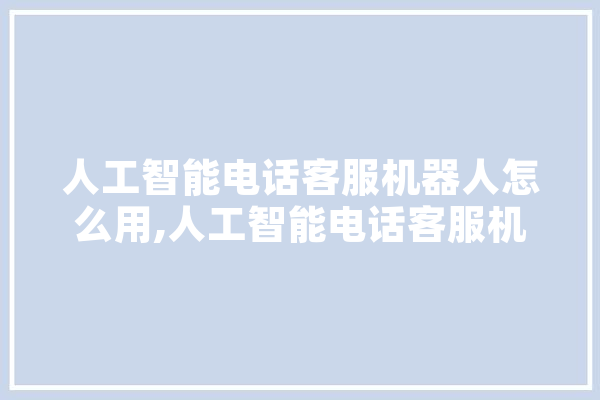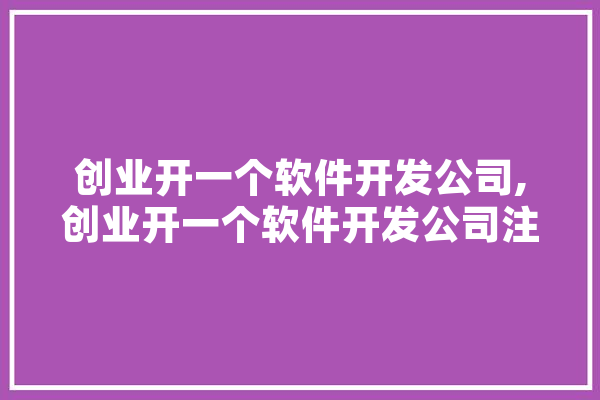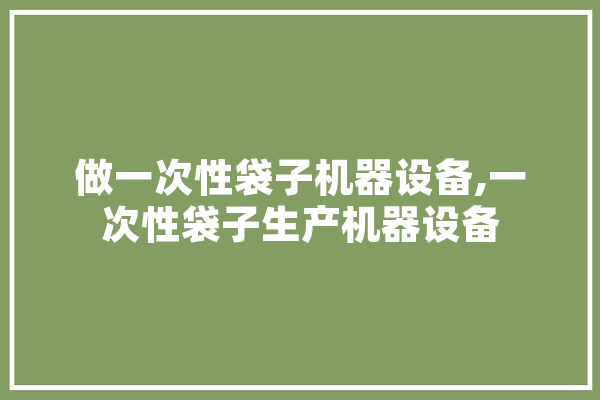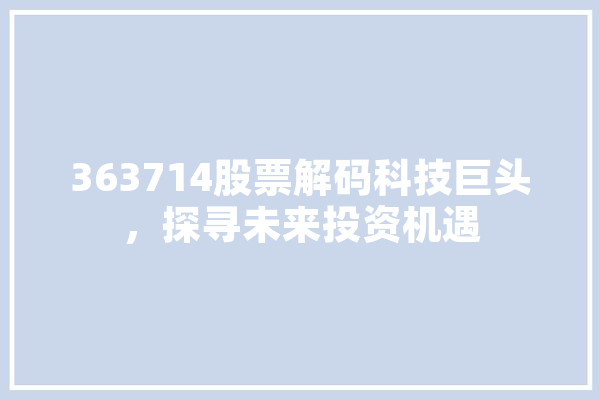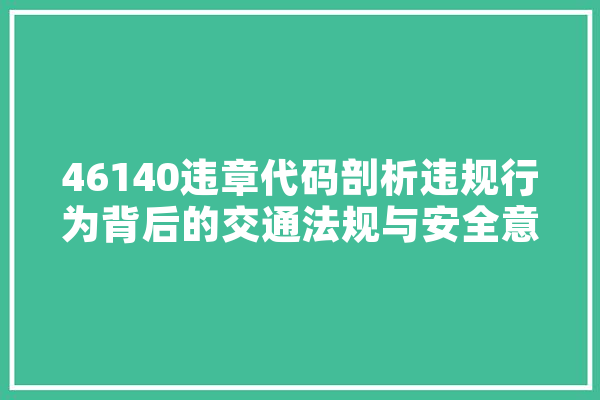人工智能设计出了人类无法理解的量子实验_光子_量子
量子物理学家马里奥•克莱恩至今还记得自己2016年初在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里翻阅MELVIN的打算结果时的情景。MELVIN是克雷恩创建的一套机器学习算法,属于一种人工智能。它的任务是将各种标准量子实验的根本模块进行稠浊和比对,借此探求新问题的办理方法。克雷恩创造,MELVIN的确做出了许多有趣的创造,但个中有一条却令他摸不着头脑。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的程序一定出BUG了’,由于这个解法根本不可能存在。”MELVIN彷佛是想通过创造多光子的繁芜纠缠态来办理问题。问题在于,克雷恩、安东•塞林格和同事们并未给MELVIN供应创造这类繁芜量子态所需的规则,但MELVIN却自己找到理解决之道。终极克雷恩意识到,这套算法创造的实在是上世纪90年代初设计的一套实验安排,不过当初那套实验要大略得多,MELVIN办理的问题则远比它繁芜。
“我们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之后,便立即对这个解法进行了归纳和泛化。”克雷恩表示。自此之后,其他团队也开展了一些MELVIN设计的新实验,以全新的方法测试量子力学的理论根本。与此同时,克雷恩从维也纳大学跳槽到了多伦多大学,和新同事一起改进了他们的机器学习算法。他们最近研发了一套名叫THESEUS的人工智能系统,不仅打算速率比MELVIN快好几个数量级,而且打算结果对人类一览无余。MELVIN的打算结果须要克雷恩和同事们花费数天、乃至数天韶光去理解,但THESEUS的打算结果则险些一眼自明。
克雷恩打仗到这个研究项目实在纯属有时。当时他和同事们想弄清,如何通过实验创造光子的量子纠缠态:当两个光子发生相互浸染时,便会形成“纠缠”关系,牵扯个中的两个光子都只能通过同一种量子状态进行数学描述。如果你对个中一个光子的状态进行丈量,纵然两个光子远隔千里,丈量结果也能与另一个光子相吻合(因此爱因斯坦称之为“幽灵般的纠缠关系”)。
1989年,丹尼尔•格林伯格、迈克尔•霍恩和塞林格三名物理学家对一种名叫GHZ(三人姓氏首字母的结合)的量子态进行了描述。GHZ量子态涉及到四个光子,每个光子都处于0或1两种状态的叠加态上(这种量子态名叫量子比特)。在三人揭橥的论文中,GHZ状态包含四个相互纠缠的量子比特,全体系统处于一种二维的量子叠加态中,要么为0000,要么为1111。如果对个中一个光子进行丈量,创造其处于状态0上,全体叠加态便会坍缩,其它光子的状态也是0;测出的结果为1也是同理。上世纪90年代末,塞林格和同事们首次在实验中不雅观察到了三个量子比特的GHZ态。
克雷恩和同事们还想不雅观察到更高维度的GHZ态。他们想利用三个光子,每个都有三个维度,即可以处于0、1、2三种状态的叠加态上。这种量子态名叫“三维量子比特。克雷恩团队想探求的便是一种三维GHZ态,处于000、111和222三种状态的叠加态上。这种量子态可以大大增强量子通信的安全性、以及量子打算的速率。2013年末,研究职员花了数周韶光设计实验和开展打算,试图通过实验创造出所需的量子态,但每次都以失落败告终。克雷恩表示:“我当时切实其实要抓狂了,为什么我们便是找不到精确的实验设置呢?”
为加速研究进程,克雷恩先是编写了一套打算机程序,可以根据实验设置打算出实验结果,然后对程序进行了升级,将光学实验台上用来天生和操控光子的根本模块整合了进去,包括激光、非线性光学晶体、分光器、移项器、全息图等等。这套程序将这些模块进行随机稠浊和匹配,组合出了海量配置,并依次开展打算、输出结果。MELVIN就这么出身了。“短短几小时内,这套程序就找出了我们这几位科学家耗费数月都没能找到的办理方案。”克雷恩指出,“那真是猖獗的一天,我至今都不敢相信这真的发生了。”
接下来,他又授予了MELVIN更多的聪慧。每次找到一种有用的配置,MELVIN都会将其加入自己的“工具箱”。“这套算法会记住这些,并试着用它们来探求更繁芜的办理方法。”
但令克雷恩在维也纳那间咖啡馆里百思不得其解的,也正是“进化后”的MELVIN。在MELVIN的实验“工具箱”中,克雷恩加入了两个晶体,每个都可以产生一对处于三维纠缠态的光子。克雷恩原来以为,MELVIN会找到一种实验配置,能够将这两组光子组合在一起,最多达到9个维度。但“它实在找到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解法,纠缠程度远比其它量子态都要高得多”。
克雷恩终极创造,MELVIN实在利用了一种近三十年前由数支研究团队开拓的技能。1991年,罗切斯特大学的三名研究职员设计出了个中一种实验方法。随后在1994年,塞林格和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同事们又设计出了另一种。从观点上来看,这些实验取得的结果都是相似的,不过塞林格设计的实验配置更大略、更随意马虎理解一些。在该实验中,先由一枚晶体天生一组光子(A和B),这两个光子的行进路线会穿过另一枚晶体,产生光子C和D。从第一枚晶体射出的光子A和第二枚晶体射出的光子C的行进路线会完备重合,都会到达同一个探测器,因此该探测器无法判断某个光子究竟是来自第一枚、还是第二枚晶体。光子B和光子D也是同理。
移相器可以改变光子的相位。如果在两枚晶体之间放置一台移相器,并不断改变移相程度,就会在探测器处造成培植性干涉或毁坏性干涉。假设每枚晶体每秒可以产生1000对光子;在产生培植性干涉时,探测器每秒可吸收4000对光子;而在产生毁坏性干涉时,吸收到的光子数则为零,由于只管单个晶体每秒产生的光子对数为1000,但全体系统却并未产生一个光子。
MELVIN的解法中也包含这样的重叠路线。令克雷恩感到困惑的是,他的算法中只有两枚晶体。MELVIN并未在实验一开始就利用这两枚晶体,而是将它们放进了一台干涉仪中(干涉仪可以将一个光子的行进路线一分为二、再合二为一)。花了一番功夫进行研究后,他意识到,MELVIN利用的实验设置相称于用到了不止两枚晶体,这样一来便可产生更高维度的纠缠态了。
除了天生繁芜的纠缠态之外,利用两枚以上晶体的实验配置还可以实现塞林格在1994年用两枚晶体开展的实验的“泛化”版本。克雷恩在多伦多大学的同事埃弗瑞姆•斯坦伯格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结果深感震荡。“就我所知,这种泛化是人类仅凭自己之力永久也想象不出、也实现不了的。”
在个中一种泛化的实验配置中,晶体数量为四,每枚晶体都会产生一对光子,有四条通往四个探测器的重叠路径。量子干涉可以形成培植性干涉,即四台探测器都能探测到光子;或是毁坏性干涉,即没有一台探测器能探测到光子。
但直至不久之前,真正开展这样的实验都一贯是一个迢遥的梦想。不过今年三月,中国科技大学研究职员与克雷恩在联合揭橥的一篇预印论文上报告称,自己在一枚光子芯片上搭建了完全的实验配置,并成功开展了这项实验。由于光子芯片的光学稳定性极强,研究职员在实验中连续网络了超过16个小时的数据,而这在大规模实验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刚开始考试测验将MELVIN的研究成果简化和泛化时,克雷恩和同事们意识到,这种解法实在和数学中一种名叫“图”的抽象表达形式很相似。图由“顶点”和“边”构成,可以用于描述物体之间的配对关系。在量子实验中,每个光子的行进路线可以用“顶点”来表示,而每枚晶体则可以用连接两个顶点的“边”来表示。MELVIN先是创建了这样一个图,然后开展了一系列名叫“完美匹配”的数学运算,即让每个顶点仅与一条边相连。这一过程可以使终极量子态的打算大大简化,不过对人类来说仍旧难以理解。
不过,MELVIN继任者THESEUS的涌现改变了这一点。它可以对第一步天生的繁芜图进行筛选,逐渐将边和顶点的数量减少到不能再少(如果进一步减少,该实验设置便无法产生想要的量子态)。这样的图比MELVIN的完美匹配图大略得多,因此更随意马虎被人类解读。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埃里克•加瓦尔坎迪对这些研究事情深感震荡。“这些机器学习技能真的很故意思。对人类科学家而言,有些解法看上去十分‘新颖’。不过就现阶段来说,这些算法离真正具备提出新想法、创造新观点还差得很远。不过,我相信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只管我们如今仍在婴儿学步,但千里之行,终归要始于足下。”
斯坦伯格也赞许这一不雅观点。“就目前来说,这些已经是绝妙的工具了。就像所有精良的工具一样,它们已经帮助我们实现了一些原来不可能实现之事。”(叶子)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