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想论坛⑤ 丨 人工智能若何改变翻译_人工智能_机械翻译
本次推送的是第五场活动“译论五丨人工智能如何改变翻译?”的现场内容宣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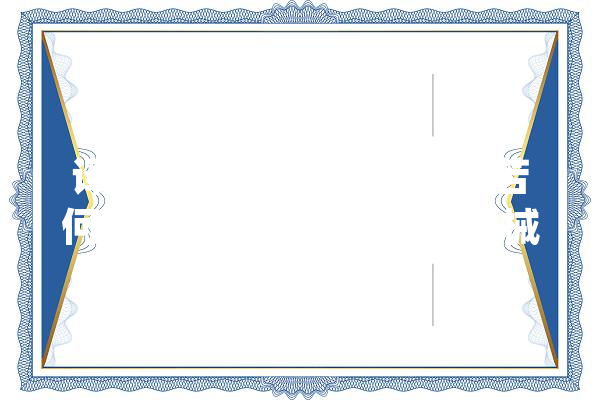
“译论五丨人工智能如何改变翻译?”现场。
采写 | 新京报 徐悦东 演习生 李颖
“我曾经在比利时留学过几年,那个地方是讲荷兰语的。虽然我们上课用英语,但学校关照都用荷兰语,我当时第一次利用谷歌来翻译,它翻译得非常准确,让我感到很震荡。”科幻作家宝树用自己的亲自经历阐述了机器翻译的“奇妙”之处。
科幻作家宝树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现在机器翻译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期。那么,人工智能在翻译领域有什么打破?它对我们的社会有若何的影响?5月14日,在由新京报·文化客厅联合甲骨文共同举办的第二届译想论坛的译论五上,宝树、刘刚与刘劲松就“人工智能如何改变翻译”这一议题展开了磋商。
在人工智能面前,
我们不需妄自菲薄
现在有很多人害怕被人工智能抢走饭碗,从去年开始,华尔街有越来越多的剖析师辞职,由于他们以为自己即将被人工智能取代。在翻译界,这种惶恐更是普遍,刘劲松说常常有人问他一个问题——“刘老师,我是做翻译的,现在我的事情是不是保不住了呢?”乃至还有大学西席见告他,教诲部建议明年取消英语专业,由于对人工智能的惶恐,现在很多学生都转专业了。
实在人工智能不是本身厉害,而是背后的专家厉害,它的翻译基于专家翻译的语料库。刘劲松举了自己的例子来解释专家的厉害之处——他以前想考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一位老师送给他两句话:文学是读不完的书,措辞学是读不懂的书。
刘劲松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时期的到来,大家如果不自己去学习新东西,很快就会后进,被时期的巨浪淘汰。事实上,我们该当去理解人工智能的上风与劣势,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过于迷信。在理解人工智能的毛病之后,我们就可以专攻它的毛病,形本钱身的上风。
另一个担忧是人工智能搜集大量的个人信息,将人置于监控之下。刘劲松认为任何技能都是双刃剑,就看人如何利用它。如果人利用了有利的一壁,比如用来剖析一个病人的肺部阴影,就可以更好地为人类做事,毕竟人工智能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而一个年夜夫的诊断一样平常只有70%的准确率。虽然坏人也可以利用它去做一些缺德的事情,但技能本身是无害的,就像原子弹一样,原子弹对中国来说非常关键,但我们不一定要利用它。
人工智能若何做翻译?
人工智能这个词是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50年代美苏争霸期间,一批美国情报局的人找到许多科学家,希望能够制作出一个别系来获取翻译情报,这个别系就叫做机器翻译。当时有很多措辞学家加入到团队里,把语法规则教给机器,让机器学习后进行翻译。
1966年,由于机器翻译得不准,CIA
(美国中心情报局的简称)
提交了证明这个项目没故意义的报告,停滞对该项目的帮助。由于要办理机器翻译的问题,这份报告匆匆使了打算措辞学的出身。到八十、九十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一批美国专家从政府进入到IBM公司连续研究,他们通过数学统计的办法来研究。比如“我想用饭”这句话,“吃”和“饭”搭配的概率比较高,机器就会记住这个搭配。
从2010年开始,我们终于有了云打算、云平台和云存储,大数据和CPU的进化版GPU也涌现了,电脑的打算能力和可视化能力大大提升。基于这些技能,2016年,谷歌翻译运用了最新的神经网络模式,在关键算法——词向量上有了打破。这时候谷歌的翻译水平已经与一样平常人差不多了,它可以根据高下文来调度翻译,在“信达雅”中“信”和“达”都做得很好,只是“雅”还没有达到。
人工智能的语料库加上神经网络,再有背后的算法工程师助力,人工智能的翻译水平会越来越高。刘劲松说他在做翻译时会有打算机没有学到的地方,这时可以靠算法工程师和扩展语料库来办理,语料库方面是吃什么长什么,它跟一个婴儿一样,想让它翻译得好就要喂它吃好东西。
想象中的人工智能,
与人工智能的想象力
在被问到读过的写人工智能最好的科幻小说时,宝树回答了阿西莫夫的《末了的问题》,这部1956年出版的小说预言了人工智能、自然措辞处理、问答系统、互联网、云打算、大数据和智能终真个涌现。它从电脑抽芽的时候开始讲述了一个辉煌壮丽故事,人问打算机AC说,如果这个宇宙会发生热寂,宇宙的熵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混乱无序,若何才能大幅度降落总熵,这个AC说:“数据不敷,无法作答。”
《末了的问题》,作者:阿西莫夫,译者:李伟才,出版社:山边社,1987年。
过了一百年又一百年,人类问了AC很多次同样的问题,若何才能把宇宙的热气逆转过来,让宇宙重新活过来?AC都无法回答。到了人类实现了永生的时候,心灵已经能与肉体分离,所有心灵和AC也便是全体宇宙领悟在了一起,人类问AC这个问题时,它仍旧无法回答。末了到宇宙快要寂灭的一瞬间,AC终于领悟了这一“末了的问题”的答案,结尾写道:AC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它完成了末了的事情——逆转熵,重新创造了这个天下。阿西莫夫把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人类历史、命运结合起来,来了一个所谓的“神改”。
刘劲松则提起了《机器之心》的作者——谷歌技能总监雷·库兹韦尔,他二十年前就知道最近十年发生的事情,他80%的预测都实现了,还有剩下的20%,可能会在本世纪剩下的80%的韶光里实现。剩下的20%展现的未来是,人不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我们身体里各种部件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来掌握,身体一旦涌现非常就会被人工智能不知不觉地消灭,人的寿命因此大大延长,人脑也可以通过植入芯片来提高影象力,达到人机合一的状态。
虽然这样的社会有些胆怯,但刘劲松希望能够在有生之年享受到这个技能,比如胳膊断了,就可以装千篇一律的,乃至更好的。
《机器之心》,作者:雷·库兹韦尔,译者:胡晓姣,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16年4月。
在人类想象人工智能的同时,人工智能自身的想象力也在进化。现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写出博客,由人设定一个场景,人工智能就可以天生一段笔墨,把人的设定填进去,现在不少人已经用这个办法来写作了,一万字很随意马虎就可以写出来。抄袭七八本书的人中就有这种情形,用机器抄袭。
对付机器创作的情结实在由来已久。二十年前,有个大牛制作了一个软件来写诗,写出来的诗很先锋,轻微改一改就可以“以假乱真”。但是诗毕竟还是纯文学,不太好做,类型文学就非常套路化,更随意马虎被机器模拟。
例如有一个人的父母被害了,他学了武功去复仇,手刃仇人后抱得美人归,这是一个很俗套的故事。但是如果说他是去邪术学校学邪术,就变成了《哈利·波特》,还可以改成超级英雄的电影。同一个套路改一改,就很可能产生一种很不错的创意,人工智能在学习后可以直接写出一部小说。
虽然这种机器创作的确缺少了一些想象力,但宝树相信未来人工智能可以进化得更好。刘劲松也表达了类似的不雅观点,他举了“一带一起”翻译的例子,现在的人工智能无法翻译它,由于这须要想象力。但人工智能的上风是极强的学习能力,它总有一天能学会这个中的窍门。
作者:新京报 徐悦东 演习生 李颖
编辑:西西
校正:翟永军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