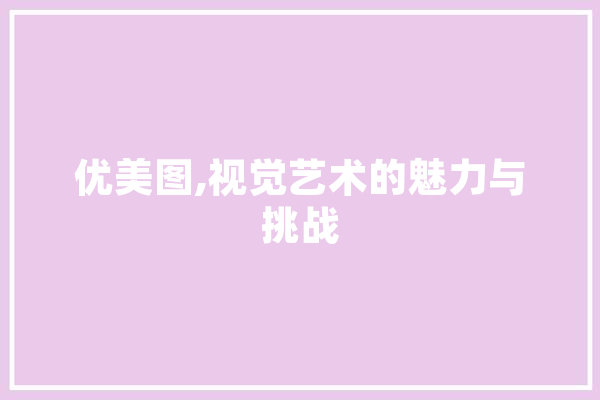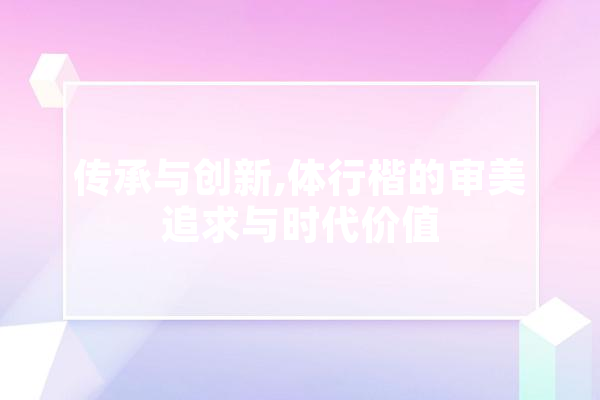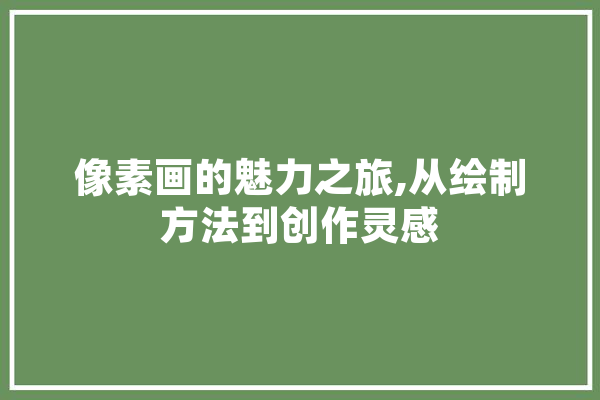人工智能让艺术与生活“兼容”_人工智能_艺术
人工智能离我们到底有多近

美国汉森机器人公司的创始人David Hanson带着他的机器人朋友索菲亚涌如今“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论坛和展厅中,跟不雅观众进行互换。这个有着真人脸庞和机器身体的机器人仿佛让我们看到了电影《机器姬》的画面,她也是首个得到公民身份的机器人。展厅内,当索菲亚跟不雅观众进行对视、微笑、互换时,不雅观众犹如面对牙牙学语的新生儿般,时时一阵阵的鼓励。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也代表了人类对付人工智能的一种态度?
机器人索菲亚在与不雅观众交谈
展厅另一侧,一个叫NIWOO的智能设计平台可以在现场输入名称和标语后,自动天生自己的logo,设计风格也可以自己选择。通过对美学原则与设计规则及数据进行深度领悟,冲破设计生产办法的壁垒。而在几年前,国外也已经有可自动天生3D设计的软件平台Dreamcatcher。“这会不会抢了很多设计师的饭碗?”被问及这个问题时,NIWOO创始人徐作彪笑称,确实会淘汰掉一部分低端设计师,但对另一部分设计师来说,更希望利用AI技能帮助设计师摆脱重复性劳动事情,让设计师更专注创意本身,这对全体设计行业来说都是一个思维模式的颠覆。
展出的陶瓷元素作品《来风·夏·芒种》
在现有智能设计实践中,已经开始涌现了一种新的设计角色——“训机师”。设计师不再是被哀求供应一个明确的设计结果,而是要设计一个机器如何做设计的过程。不同于艺术与科技展的其他展品观点性的展示,这个智能设计平台即将投入市场,未来人们可以花很少的钱就得到一些根本的设计,“我们向公众年夜众开放后,设计师可以向我们供应一些新的设计规则,他们也会从中得到一些设计分成,这更方向于创意本身。”徐作彪说道。
各类迹象表明,人工智能时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人工智能(AI)参与艺术更是早就有了端倪。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艺术不再是人类专属,人工智能参与艺术已见趋势。”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鲁晓波说,“以前我很自傲地说,人工智能玩艺术还早呢,没想到很快在很多领域都有新的打破”。
比如之前由人工智能(AI)创作的艺术作品《埃德蒙· 贝拉米肖像》在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以43.2 万美元(约合300万元公民币)的高价拍卖成交,引起关于艺术边界的磋商与震撼。中国的人工智能少女画家微软小冰在中心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首个个人画展……
科学技能,早已无所不在地充斥并影响着艺术。就像我们常常在展览里看到的VR、交互、虚拟、稠浊现实、生物基因……跨媒体与跨学科的呈现,技能与伦理的磋商,人工智能与艺术家的角色,无论是艺术还是艺术家的身份,边界一次又一次被试探被打破。而科学+艺术已经不仅仅是博眼球的短暂鼓噪,而成为艺术发展的现实问题和严明思考。
显然,艺术界早就感知到这种趋势。仅仅是最近一段韶光,11月3日,“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11月2日,重磅大展“科技艺术四十年——从林茨到深圳”上岸深圳海上天下文化艺术中央;11月7日,“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与EAST-SCA圆桌论坛在明当代美术馆举行;还有即将在2020年1月举办的CAFAM Techne三年展,同样磋商科技、艺术与文化交叉发展之下艺术的新出路。
对艺术的重新定义
回忆三年前,艺术界磋商科技对艺术的影响,更多的还是关于磋商视觉效果、技能本身对艺术的影响。而如今再磋商同一主题,无论是展览还是论坛,纷纭将科学与艺术这一话题指向另一个关键词:人工智能。这也是“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和“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展览”与EAST-SCA论坛共同选择的主题方向。
“目前面对人工智能、3D打印等这样全新的技能寻衅,清华大学联合国家博物馆共同主理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和学术研讨会,磋商人工智能给人类社会、家当、文化带来的诸多寻衅,并展现出多样化和探索性的创新办理方案。”本届展览和研讨会的实行策展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清华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院实行院长赵超认为,这次活动,在人工智能推动的艺术与科学协同共创的领域里,呈现出更为广泛的国际化特点和对学科未来发展的引领性力量。在这次活动中,不仅有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对话谈论,更有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互助演讲,这首创了艺术与科学对话共创的新范式,在国际上的干系学术领域是一种全新的探索型考试测验。
“人工智能”这一观点出身于1956年的达特茅斯会议,近年来,以大数据、云打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发展日月牙异,人工智能通过不断进化迭代,基本实现感知能力,并从感知进入认知领域。“这个时期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人工智能经历了第一代知识驱动和第二代数据驱动后,现在进入第三代人工智能时期。”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阐释道:“第三代人工智能便是把前两种办法结合起来,这个想法跟我们艺术创作的很靠近。”
张鏺与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正在研究的人工智能已经能做出靠近人类创作水平的诗歌,但在音乐、绘画、写小说方面,“它还得努力”。它创作出来的艺术,能算艺术吗?工业革命带来人类新的物质文明,人工智能能否带来人类新的精神文明?张提出这样的疑问,也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按照图灵测试的标准,知识或者数据加上算法和算力也可以产生智能,这是我们的不雅观点。艺术的魅力在于它创作的空间非常之大,以是打算机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那些过去人类未涉及到的空间。这也给艺术人工智能供应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这对人工智能是一种磨练。”
不雅观众体验作品《存档梦境》
试想,如果像电影里一样,人工智能实现打破,能够完全感知、认知、决策、实行和处理人类的哀求和活动,将会为天下带来无穷的想象。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的“大脑活动图谱操持”、欧盟的“人类大脑项目”、日本的“脑/思维操持”以及中国的“中国脑操持”相继以脑认知为出发点,
重点环绕人工智能展开。而艺术要磋商的,或许则是关于人、关于艺术的重新定义。
没有边界的认知天下
为何将科技和艺术这两个学科放在一起?李政道和吴冠中两位师长西席早已给出了答案。李政道曾说:“艺术与科学是一枚***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性。”1995年和1996年,吴冠中为李政道所主持的科学会议分别创作了名为《对称乎,未必,且看柳与影》和《流光》两幅主题画。一位诺贝尔奖得到者的物理学家和一位有名海内外的老画家,开始联手倡导艺术与科学的结合。由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艺术与科学结合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事实。
2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欲望已然成真。尤其是当代艺术里的科技身分,溘然在本日进入爆发式的利用阶段。两位师长西席倡导的不雅观点,也从来没有像本日这样受到如此广泛的追捧。鲁晓波说:“目前环球有很多热点,而科学与艺术的领悟正是热点中的热点。”大概正由于这两个学科是人类创造力最闪耀的地方。我们在这样的结合中欣赏创造的魅力,也仿佛能一窥未来的门径。
历史见告我们,任何一个技能创新生动的时期,无一例外都伴随着人文创新的勾引,文化与科技的互动推动了人类创新和文明的发展。在鲁晓波看来,科技史和艺术史从未分开过。“科技艺术自古有之,从来都是密切地在一起事情的。只是到了最近的两三百年,被近代的学科分科体系,人为地分割成了科学学科和艺术学科,我们看到在达·芬奇和丢勒的时期,这样的分割实在还都没有涌现过。文艺复兴经典之作是得益于对透视学的创造和理解,才能塑造出具有震荡性的艺术作品;从工具层面,油画油料提升技能,对油画的表现力也有极大的提升;印象派对光学的认识带来了新的艺术风尚;在工业化时期,动态雕塑大行其道;数字媒体时期,天下各大美术馆都有新媒体专馆。”
德国卡尔斯鲁厄国立设计学院的教授Gerhard Ludger Pfanz在未来设计学院思考我们如何设计未来本身,并进行跨学科的研讨。他认为,AI是缪斯,AI不是做出所有的选择,而是给他很多的选择性,这是很故意思的办法。不仅仅是用AI代替艺术,而是给我们一个新的产生灵感的工具。从更大的角度说,新的趋势下,智能事物的网络,同时利用可再生的能源,这便是未来的系统。
在这次展览展出的作品中,王之纲、孙瑜的沉浸式新媒体艺术作品《城市影象》是对人与科技互动发展关系的艺术化探索与表达,引发不雅观众对未来人与科技关系的思考。浮思★事情室的作品视听装置《多重宇宙.pan》通过创建一系列实时天生的数字绘画,来考试测验描述无限平行宇宙的永生和永逝,永恒和无限的观点也通过不雅观众和艺术品互动的形式得到了表示。兰塞和马特的作品《共享感官》通过脑机接口(BCI),让人类和AI实现亲密体验共享,在共享的镜像神经反馈系统中,他们一同奏响“亲密感数据交响曲”。
展览作品《宙蝶》局部
新技能的利用同时拓宽了人类的认知天下。正如朱文婷和梁琰的作品《重现化学》通过微不雅观拍照,从客不雅观的角度创造并展现化学之美。在新的视野下,统统创造都没有边界,统统探索都不在于诉说一个答案。
不雅观众在与作品《鸟鸣钻石》互动
新的认知、伦理和寻衅
在这样一个被法国技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明确描述的技能社会与技能秩序下,在过去强调专业细分和社会分工的背景下,技能与艺术彷佛成难堪以兼容的对立面,更进一步,艺术给人们带来的想象力、共情能力、非丈量性以及个中所包含的时期审美与代价判断,引发人类的本能力量,产生新的创造力,让人们在前行变革的技能社会中不断适应新的人工环境,不断找到人机物新的互助办法。
而对付人工智能的利用,并不是所有艺术家都那么乐不雅观,许多作品也在磋商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人类认知、伦理和寻衅问题。作品《脑机接口》采取反射微蚀技能,以未来人脑互连为主题,描述强大的神经接口技能惊人的上风和潜在的危险,提醒人类以谨慎的乐不雅观态度发展这一技能。不雅观众从蚀刻画左侧向右侧移动时,神经元的突触会形成类似恐怖面孔的形象。这象征普通人对人类/机器进化未来的恐怖,特殊是对目前正在利用的更具侵入性植入技能的恐怖。随后,蚀刻画会转变为对进化成功的敬畏、释然和喜悦的表情、比如成功规复失落去的功能、成功增强人类的认知和互换能力、成功提升我们对信息的获取能力等。末了,电流从面部喷涌而出,象征进化会增强人类的潜能。当不雅观众从右侧到左侧不雅观察蚀刻画时全体过程是相反的:人类通过利用这些技能达到了神性化状态,末了却由于不合理滥用这些技能而沦为了受害者,导致了人类灵魂的堕落。
而吴琼、张益豪的作品《人工智能的活肖像》利用感光细菌为人工智能创造的“均匀不雅观众”天生一张活肖像。作品为每天到访的不雅观众拍摄一张照片,这些照片经由人工智能算法天生到访的“均匀不雅观众”形象,并被转换为光旗子暗记,驱动经由基因编辑的 感光细菌,天生“活”的、虚拟人物的肖像。作品借用合成生物技能为人工智能创造的虚拟人物留下了生物的痕迹,匆匆动人们思考在智能的鸿沟被填满后,生物属性会是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实质差异吗?面向未来,我们该如何理解什么是天生?什么是存在?
参展作品《自我映射》局部
正如鲁晓波所说,当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科学技能不断进步,新的不雅观念不断呈现,艺术虽然更加多元,但彷佛失落去了原来共有的范式——对美的追求、对本体内力的坚守。在探索新方向的过程中,人文代价尤为主要,艺术与设计,便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情怀驱动创新。任何一个技能创新生动的时期,无一例外伴随着人文创新的勾引,强调艺术与科技的领悟,重视技能手段的创新与艺术思维的交融,倡导人文和科学共创未来,这才是人类走向和谐永续的必经之路。
(文章来源于中国美术报 )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