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批评与回应_人工智能_法学
人工智能的干系观点已越来越为法学研究者所熟知,但也引致一定批评。干系争议紧张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法学研究者缺少干系打算机专业知识,难以深入研究此类问题;二是此类问题并非一个真正的法学问题,而只是一个详细的征象。仔细思考即可创造,这两类批评见地均不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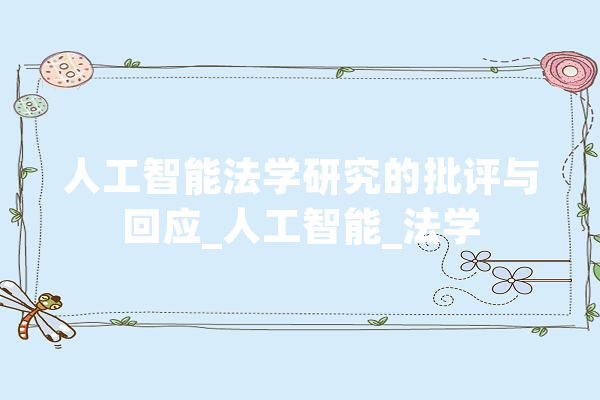
对付第一类批评而言,法学研究的工具是技能引发的法律问题,但并不研究技能本身。诚然,在研究技能引发的问题时,虽然技能本身的知识非常主要,但远远没有达到须要精通技能的程度。以知识产权为例,绝不能认为法学研究者因没有理工科背景,而无法研究知识产权。干系技能引发的知识产权问题才是法学研究的工具。因此,法学研究者只须要知晓技能与对应法律问题之间的逻辑联系,而无须稽核技能本身。又以人格为例,法学关心的仅仅是自然人、法人的法律主体地位及其法律关系。历史上,法大家格拟制说、法大家格实在说的辩论,也仅仅是关于法人意思表示的形成办法的辩论,而绝不会去研究自然人的脑科学布局或法人的“精神天下”。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误解,才导致许多人缺点地从人工智能的“聪慧”出发,倒推论证其法律人格的可能性。
事实上,人工智能的法学研究本身即可分为人工智能问题的法律化以及法律问题的人工智能化两大议题。在实质上,只有人工智能问题的法律化才是法学研究的工具。而须要深厚人工智能技能知识支撑的是法律问题的人工智能化。其本色上是人工智能问题而造孽学问题。范例如法律人工智能的构建,即通过打算机科学与逻辑学的方法,将法律代码直接转化为打算机代码,致力于实现“莱布尼茨之梦”,构建出人工智能时期的“自动售货机式法院”。这些问题本身属于人工智能法律运用的技能培植,不属于法学研究的工具。在这类技能培植中,法学研究的方向只能是聪慧法律与法管理念的抵牾、现行制度的冲突、新型制度的构建、法律风险的戒备等问题。
对付第二类批评而言,人工智能问题的法律化究竟是一种类型化的法学问题还是具表示象中的法律适用问题,直接关系到“聪慧法学”“数据法学”“网络法学”等新兴学科的代价和意义。早在20世纪末,网络法历史上即存在著名的“马法之议”。有学者认为,网络法实际上毫无意义,如果关于网络可以存在网络法,那么便可得出关于马也存在“马法”的荒谬结论。这一见地与对人工智能法学研究的第二类批评高度吻合。然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互联网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电子商务、网络平台、数据处理、信用评分等法律问题的主要性日益显著。网络法也已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畴与研究范式。
在人工智能时期,网络法的进一步发展必须面向人工智能。以“机器学习”为根本的人工智能技能已经对“不学习”的法律制度构成了颠覆性的寻衅。智能算法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法律问题,如通过“算法同谋”形成垄断,利用“电子产品动态定价”技能进行“大数据杀熟”,通过数据挖掘与还原技能节制用户的“数字人格”等。此外,人工智能算法还可能出错,如将普通人缺点标注为犯罪嫌疑人、将乘客缺点标注为胆怯分子、将“无家可归者”缺点标记为“乞讨者”等。然而,现行法律却难以逐一回应这些问题,涌现了法律的功能危急。对此,乃至有学者发布了“法律的去世亡”。同时,人工智能也被称为“智能利维坦”。对此,有学者提出了“数字人权”为代表的“第四代人权”。正是在这些独特的议题上,人工智能法学研究逐渐走向了成熟。
值得把稳的是,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必须避免落入“科幻法学”的误区。与关于技能现状的“科技法学”不同,“科幻法学”充满了文学的色彩与丰富的想象。其常以各种著名科幻小说为工具进行想象、剖析和论证,如阿西莫夫的“机器人法则”就常被提及。《银河帝国》《2001太空漫游》《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三体》等经典科幻作品已经成为部分法学家的研究工具。然而,科抱负象并不属于法学研究的范畴。如果要研究人工智能的科抱负象,是不是也可以研究火星殖民的法律?乃至进而是不是可以研究哈利波特系列“邪术法学”“玄幻法学”“奇幻法学”?显然,这是无比荒谬的。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必须把稳避免此类假问题,应坚持从人工智能实际运用所产生的现实法律问题出发,深入研究聪慧社会变革中真正的法律问题。
综上,人工智能法学的研究工具是人工智能技能利用中呈现的法学问题,具有主要的现实意义,是未来法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干系问题的研究,既非“蹭热点”的时髦,亦非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奇迹。
(本文系教诲部人文社会科学方案青年基金项目“人工智能致害任务:法理根本、致害类型及归责路径研究”(19YJC82001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