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工智能具备了主体意识_人工智能_诗歌
一是符合语法不即是具备意义。乔姆斯基指出,“无色的绿色想法在狂热地就寝”这样的句子在语法上成立,却是荒谬无理的。当然,诗有“无理而妙”者,但“妙”仍须诉诸人类奇妙的觉得和履历。诗歌创作的关键,就在于作者能分辨诗句好坏。如果人工智能创作的诗句须要人类筛选,那它只是赞助写诗的语料库,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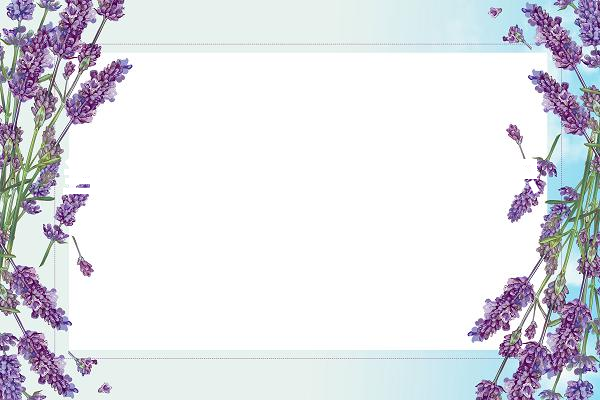
没有生活履历的人工智能能否节制诗歌的分寸?随着技能发展,人工神经网络将能精确模拟人类神经元的刺激-反应,然而好诗引发的情绪层次十分丰富,能否约化为某种模式,还是一个问题。其余,人类个体始终在推测与剖断他人的意图,这样的“主体间性”贯穿于人类阅读诗歌的过程,而人工智能将人类作为整体认识,缺少主体之间的交互;办理这一难题恐怕还要等待具有自主意识的强人工智能涌现。
二是人工智能的诗义可否理解。套用“会话隐含”理论,言语背后必有企图。在阅读诗歌的过程中,读者也在追索诗句背后的所指。威廉·燕卜荪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说:“墨客将两个陈述放在一起,彷佛二者是相互联系的,而读者则被迫去考虑他们的联系,还得自己去设想诗文为什么选择了这些事实。他会设想出各种缘故原由,并在脑中将它们排列起来。这是诗歌措辞在利用方面的基本事实。”读者设想联系的条件是确有联系,也便是说,必须有作者将联系埋藏在字句中,等待读者理解。目前人工智能写出的诗仅仅是符号的组合,没有所指,没有隐喻,读者的统统追索将成徒劳。
英国墨客约翰·德莱顿说:“‘墨客’的意思便是‘制作人’。”汉语中,诗的定义见于《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无论“制作”还是“志之所之”,都强调诗是某种意图的产物。这样看来,目前尚不具备自主意识的人工智能写出的“诗”是否名副实在,有待深入谈论。
三是人工智能写诗有无首创能力。诗不同于类型文学,强调独特性,一首好诗的代价每每表示在“前所未有”上。这和围棋不同。人工智能学习围棋,是对已有棋路的破解;而要创作精良的诗歌,则要避免已有套路。围棋是繁芜的大略问题,诗歌是大略的繁芜问题。围棋本身是一种抽象——棋盘的交叉点仅仅代表位置,所有的打算发生在规则层面,因此即便它的打算量十分浩大,仍比无限且难以分割的现实易算得多。诗歌则牵扯到符号、现实、个体、标准等诸多层面。这是摆在人工智能面前的艰巨任务。
四是人工智能写诗的必要性。诗歌并非生活必需品,不以量取胜,又无十分明确的评价标准,有无必要花费巨大代价开拓人工智能写诗的能力?对诗歌来说,这恐怕没有直接的裨益。而对人工智能来说,真正诗歌创作的条件是主体意识。我们可以设想,一旦拥有主体意识、具备情绪和措辞能力的强人工智能涌现,写诗便是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程羽黑,系中山大学特聘研究员)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