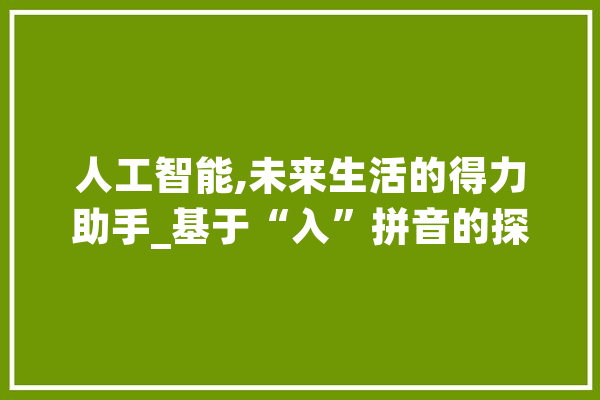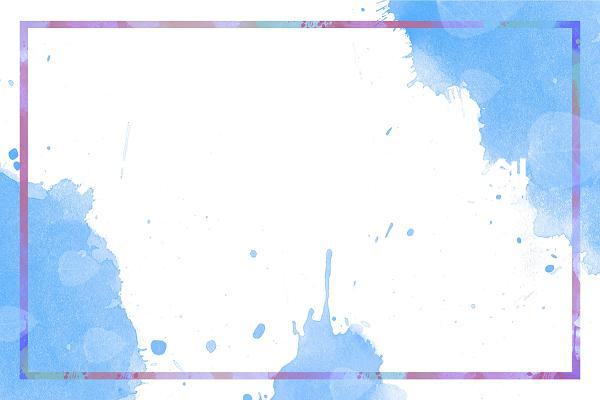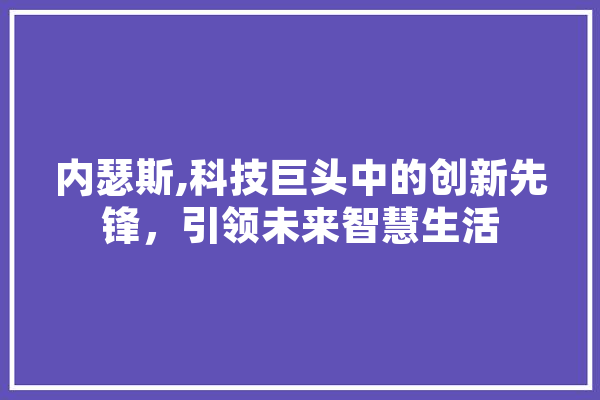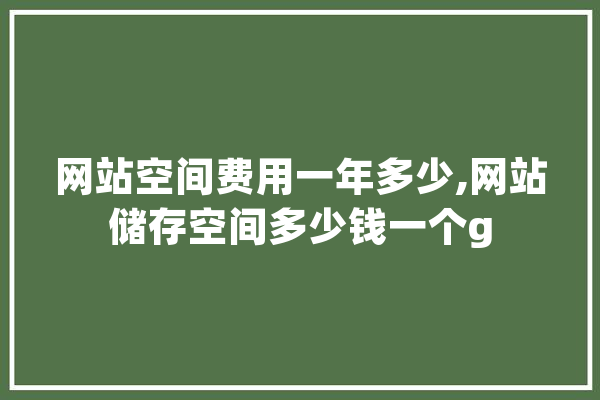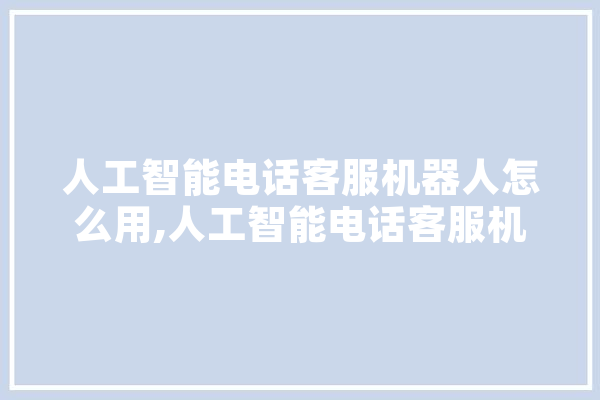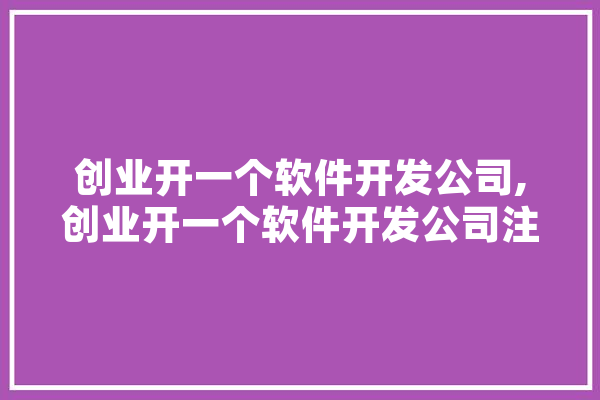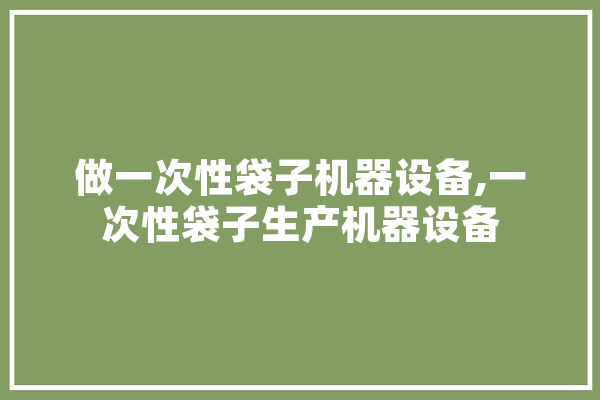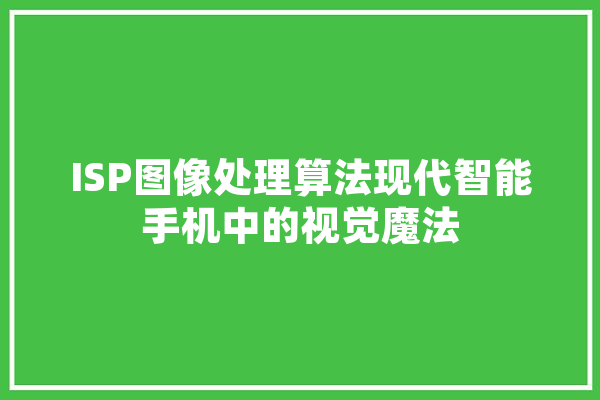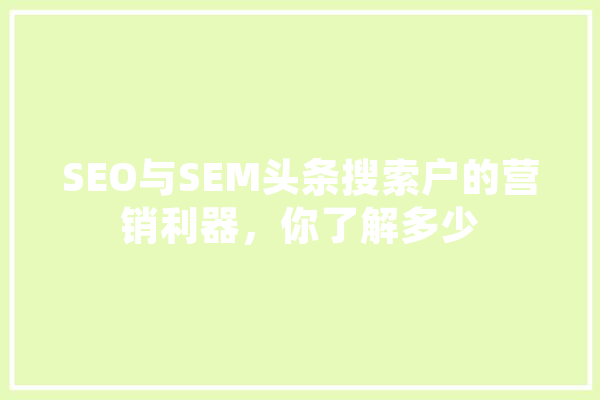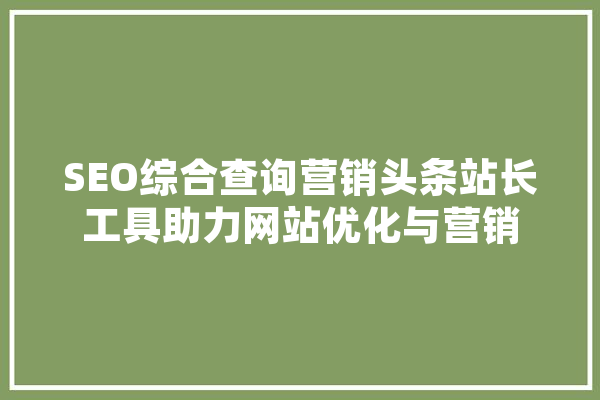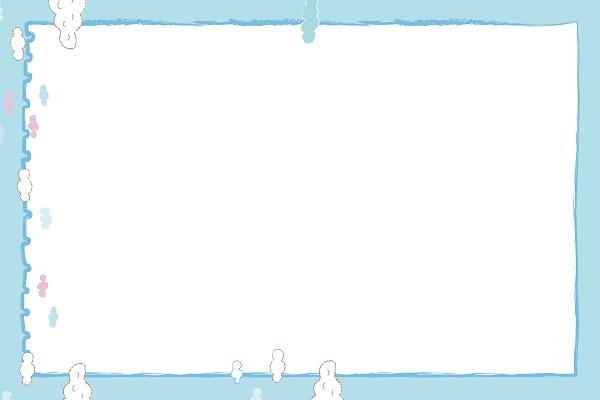人工智能没有抛弃非洲公民_非洲_人工智能
文 / 艾森

在CES2020大会上,我们把稳到了一个并不起眼的事实:超过450家人工智能参展商名录中,仅有23家企业来自非洲。个中,摩洛哥霸占了11家、埃及9家,塞内加尔3家。
有趣而在情理之中的是,农业和医疗是这些非洲人工智能公司的强项。比如一家叫Dictaf的塞内加尔公司,旨在用无人机、SOS-Agri等人工智能供应农业及医疗做事,为当地青少年和妇女就业做出贡献。
Dictaf等非洲公司正是非洲人工智能家当的缩影,在多彩如万花筒般的CES展上,他们以不能再朴素的姿态提醒着我们:这个天下有七个大洲,非洲是个中不可忽略的力量。在人们为特斯拉、脑机接口和各种令人炫目的智能设备倾倒的同时,非洲公民的每一天都在用人工智能办理更直接的问题,比如粮食,比如药品,比如如何让贫民窟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诲。
同样,来自非洲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们正肩负着他们这一世代的任务,这群年轻人彷佛便是为理解决这两个问题而出身的:一,将实用的人工智能技能用在有用的地方。二,努力实现非洲科技的本土化,为此与科技殖民化相反抗。
为了这两个目的,他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科技公司和学术机构,形成了一种既依赖又当心的共生关系。
胡椒树下的主要聚会多少年后,当人们试图用一个图案来代表非洲人工智能家当,他们可能画出一颗胡椒树的形象。
2019年8月,在肯尼亚都城内罗毕的这颗拱形常青胡椒树下,非洲大陆上的数百名本土人工智能研究者聚拢到了一起。两年前,这些年轻的非洲人工智能研究者成立了一个名为Deep Learning Indaba的人工智能学术会议,旨在为非洲的人工智能行业探求未来。
Indaba成立于2017年,这个祖鲁语(zulu)词汇意味“主要的会议或聚会”,由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大学和干系的非洲科技研究者联合成立。在这些非洲青年才俊的眼里,Indaba是一个不得不成立的组织,由于对付他们而言——无论客不雅观缘故原由还是主不雅观缘故原由——西方人工智能天下并不太友好。
客不雅观缘故原由非常大略:这些非洲地区的研究者们要参加一次西方学术会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以人工神经网络领域的著名会议NeurIPS为例(它的前身是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NIPS)。这个会议的举办地点每每在欧美发达国家的五星级酒店举行,纵然获邀参加会议,参会者也要付出颇为高额的经济本钱,更别提在2016年前,还没有一个非洲国家的申请文件被会议接管过。两年后,当100多名非洲研究职员试图参加加拿大的NeurIPS会议时,他们全部由于签证问题被拒之门外。
根据Indaba创始人的说法:“在现在机器学习领域中,被采取的论文中有多少是由非洲研究职员撰写,或者是仅作为作者之一?答案是:零。在当代机器学习领域,不存在非洲大陆的研究。”
布鲁斯·斯威利主演的电影《太阳泪》里有一句著名台词:“上帝已经抛弃非洲了”。Indaba成立之前,这句话在人工智能学界也适用。
恰是以,Indaba的本土化努力在一开始就得到非洲大陆多数国家的强烈反响。第一届Indaba会议有近750人申请,300人被约请参加。第二年,这个数字提高到了400人。而在2019年,已经有700名参会者和27场IndabaX活动。54个非洲国家里,有超过40国参加了Indaba会议,既谈论自动驾驶、自然措辞处理和人工智能伦理这些行业标配话题,也谈论如何用技能让非洲的农业、医疗和交通得到更直接的改进。
着眼于“本土化”的努力,Indaba为人工智能社区Deep Learning Indaba制订了明确的议程: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泛非洲科技(pan-African tech)社区——不是通过改造现有技能,而是为该地区所面临寻衅:弘大的交通体系、保险索赔支付困难和干旱状态,创造适宜的办理方案。一个不受硅谷掌握的人工智能社区,是Indaba创立的初衷。
但在人工智能这样的前沿科技领域,如此“高科技”的社群光靠非洲人自己是不敷以运转起来的。无论在学术还是经费上,他们都不得不与国际科技巨子有所关联。在这次Indaba的活动中,就有来自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大公司共计30万美元的帮助。
与科技巨子们有所互助,但不依赖他们。保持对西方科技殖民的当心,培养本土化人才,同时学习前辈研究、紧跟前沿科技潮流。Indaba在做一件两难的事情。
跨国公司的非洲任务科技巨子们像上帝和学术机构一样“抛弃非洲”了吗?事实证明,跨国公司敏锐得多、也务实得多。远在非洲科技市场还没取得足够的发展时,他们就已经动手进行布局。
2013年,敏锐的IBM Research就在内罗毕开设了第一个非洲办事处,又接着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开了第二个。内罗毕和南非也因此成为了非洲人工智能研究家当的两个桥头堡。
就在去年,此前一贯沸沸扬扬的“谷歌要在非洲开设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传言终于尘埃落定:他们将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地址选在了加纳的阿克拉。设立实验室之前,谷歌还和盖茨基金会做了一件同样的事情:与坦桑尼亚的农人们互助,利用人工智能提高粮食产量。
谷歌建立实验室的目的十分务实:为研究职员供应开拓人工智能产品所需的工具和环境,以办理农业部门在全体非洲大陆面临的诸多问题。其余,利用人工智能改进医疗保健也是实验的重大任务:人类的康健、植物的康健、粮食安全,这些问题只有在非洲才能切实感想熏染到其紧迫性。
除了IBM、微软和谷歌外。就在今年,一个主要的人工智能研究会议 ICLR 将在埃塞俄比亚的都城亚的斯亚贝巴举办。
专注根本研究,试图通过长期的投入环球康健科技和康健问题供应办理方案,这是科技巨子在环球化中扮演的主要角色。但同时,科技巨子们对非洲的渗透(无论主不雅观与否)也带着强烈的殖民色彩。
BBC此前曾宣布,在非洲最大的贫民窟——肯尼亚都城内罗毕的基贝拉(Kibera),有1000多人在非盈利组织Samasource的帮助下,为谷歌等硅谷大型科技公司的人工智能研究供应数据标注做事。
这1000多个在贫民窟的非洲人,每天的任务是在八小时的事情韶光内建立演习数据,把图像加工成打算机可以理解的形式。须要标注的图片信息包括人、车、路牌、车道标记乃至天空。
他们的事情既普通又主要,为了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一名上级会卖力检讨事情。当员工的效率和准确率达到最高哀求时,他们会得到购物券作为褒奖。这些数据标记工的日薪是9美元,远高于当地2美元的均匀薪酬。Samasource因此帮助了大量当地贫民窟的人改进了经济生活。
在巨子阴影下穷汉通过事情得到了更好的收入,科技巨子雇佣廉价劳动力节约本钱,你很难不承认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但这个“好办法”同时也带上了范例的殖民地烙印:这样的故事,是不是让你自然地遐想到了富士康?
最少,一位非洲的博士阿贝巴·比尔哈恩(Abeba Birhane)便是这样认为的。她将外国投资和数据网络行为与西方国家对非洲大陆的殖民行为挂钩。在最近揭橥的一篇题为《算法殖民非洲》(the Algorithmic Colonization of Africa)的论文中,她写道:“这种‘挖掘’人类获取数据的论述让人想起殖民者的态度,他们流传宣传人类是可以免费获取的原材料。”
其余,国际巨子的影响力让非洲原来起步就比较晚的人工智能企业难以得到更好的发展:他们注定无法与跨国大公司竞争。南非科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西里达兹·马尔瓦拉(Tshilidzi Marwala)对此提出过一个例子:南非原来有一个本土搜索引擎——Anansi,它能网络大量本土数据,但它不是谷歌的对手,在2011年彻底失落败了。若问环球排名第二的搜索引擎是哪个,可能大多数人都答不上来——是微软的必应(Bing)。然而在谷歌的影响之下,纵然排名第二也还是举步维艰。微软尚且如此,何况是一个非洲本土企业?
在巨子的阴影下,非洲的人工智能企业纵然实现了技能落地,也难以形成比较大的规模。像以支付平台有名的尼日利亚明星金融科技公司Kudi(你可以把它视为非洲的支付宝),截至2019年春天,融资规模也仅有510万美元。成立于2014年的南非农业科技公司Aerobotics,通过通过无人机、卫星和人工智能为用户供应农业数据,目前得到了480万美元的融资。肯尼亚农业信贷平台Apollo Agriculture则融资了160万美元。
这些公司上百万美元的融资规模,在非洲科技公司中已属俊彦。大部分的非洲人工智能公司,如肯尼亚的社交媒体做事供应商推举平台Utu Technologies、埃及两家人工智能谈天机器人公司Botme和WideBot,这些值得关注的企业目前的规模都在5万美元以下。
除了大略雇佣非洲的廉价劳动力以外,科技巨子们还通过投资来未雨绸缪。早在非洲75%的地区乃至还无法上网的情形下,国际科技巨子们就盯紧了非洲巨大的投资机会。由于越早与用户建立紧密的联系,就越有望在长期的用户投入中收成丰硕的回报。
背靠科技巨子的大树好乘凉,但殖民化的危险也无处不在,这是Indaba的创始人一开始就意识到的问题。Indaba对此的选择是“周旋”。
创始人在第一次会议后写道“Indaba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国际组织,我们的许多国际演讲者都来自国际科技公司。这可能会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即在大型科技公司,以及在非洲大陆以外的国家才能找到最好的事情。一个人必须离开非洲大陆,才能在该领域拥有有影响力的职业生涯。”
接管国际组织的资金声援的同时,这些Indaba成员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来自尼日利亚的科学家阿德坎姆比希望在未来10年内能够培训100万尼日利亚数据科学家。为了防止非洲科技人才流向外洋(实在你防止不了),他选择启动一个“数据科学家随需应变(Data Scientists on Demand)”的项目,帮助尼日利亚的工程师远程为天下各地的公司事情,并借此,希望那些与非洲互助中获益的公司,能够真正在非洲建立公司,并通过投资源地的技能社区来表明自己的承诺。
“周旋”的阶段性成果是,经由三年的努力,不断浮夸会议规模的Deep Learning Indaba终于在2019,将两名Deep Learning Indaba 洲际竞赛的获奖者送上了他们的应许之地—即前文提到的NeurIPS。在那里,不再被拒签问题所困扰的几位非洲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将会寻求平等的对话。
结语当我们评论辩论“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在评论辩论什么?我知道人工智能意味着未来,意味着自己能跑的无人车、脑机接口、太空旅行、《疑犯追踪》里令人无处可逃的天网、跟机器人谈恋爱。也意味一些不那么“黑科技”的场景,比如让门自动打开、你家的灯自己亮起来、或仅仅是在鞋子上装个芯片丈量你的数据。
这些场景都已经和“人工智能”一词镌刻在了我们的脑海中,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没故意识到原来人工智能还可以用来做一些最根本、最美好的事物:比如让粮食增产不受害虫滋扰,比如消灭疟疾。这正是非洲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们努力在他们自己的地皮上实现的日常。
比较之下,非洲人工智能家当当前的发展让我们看到了发达的活气,以及某种可称之为“初心”的东西:将实用的技能用在有用的地方。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还有更好的用场了吗?或许非洲公民远比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代价。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