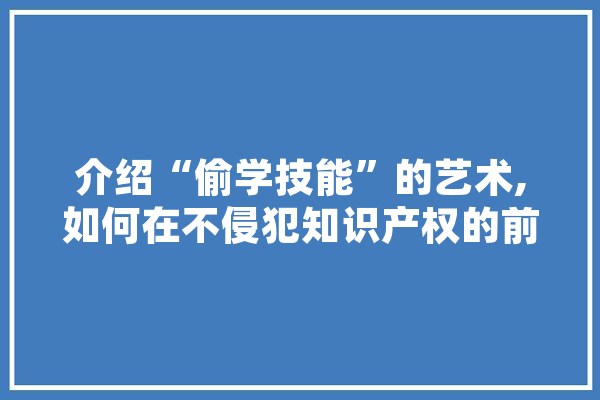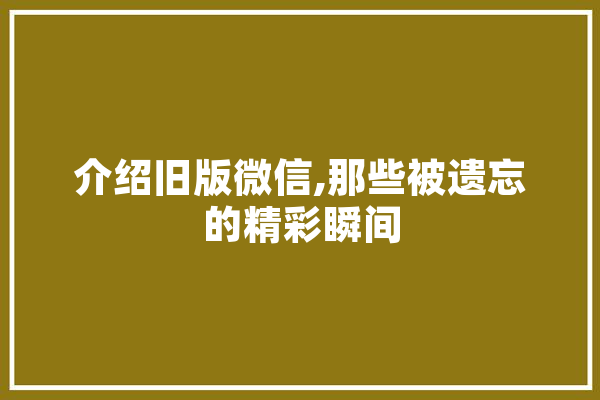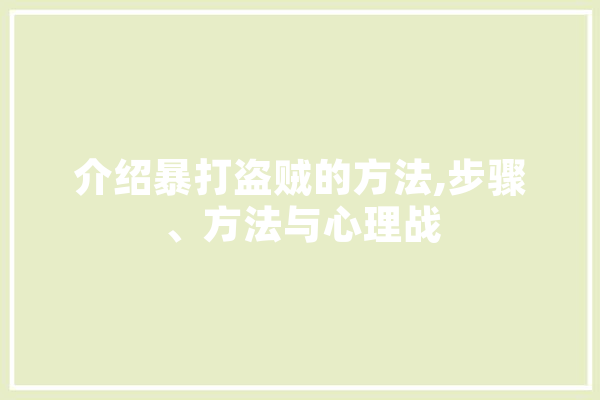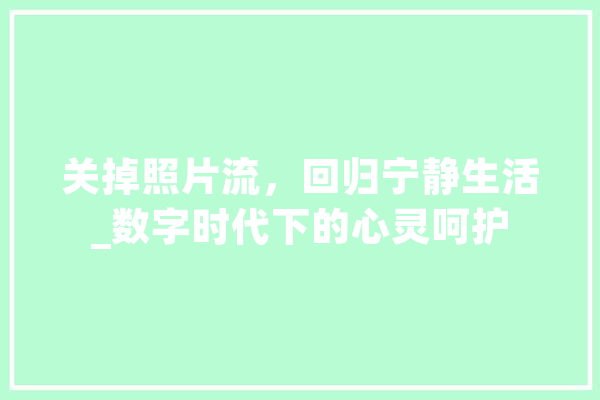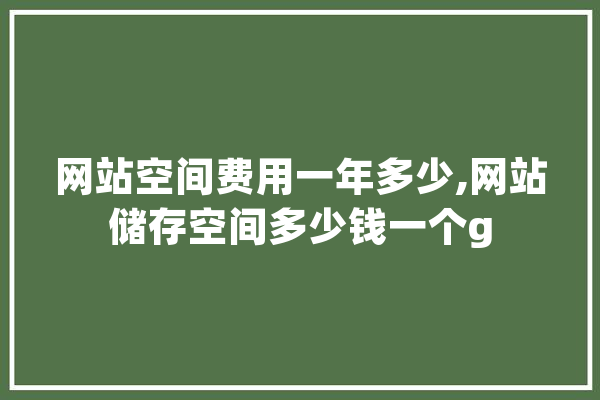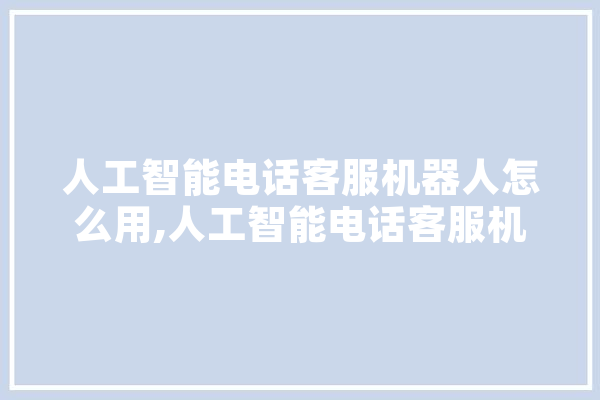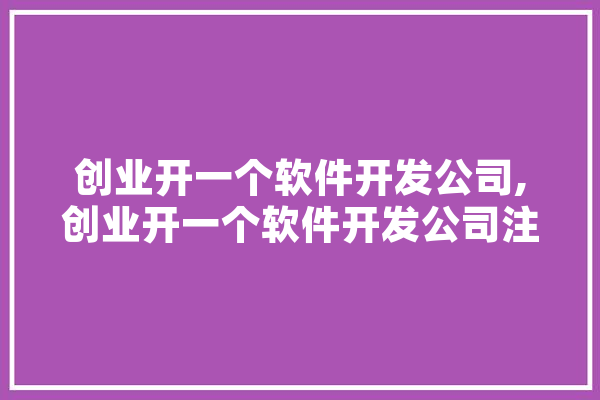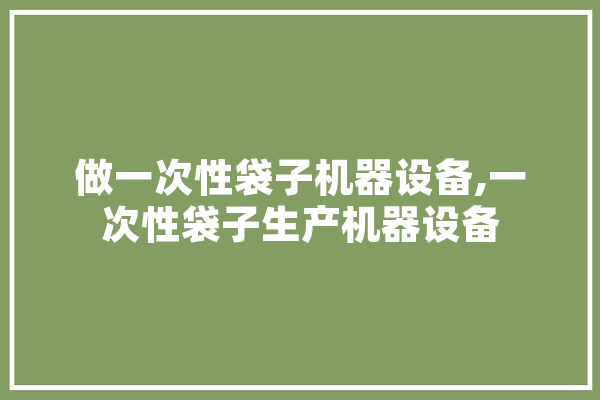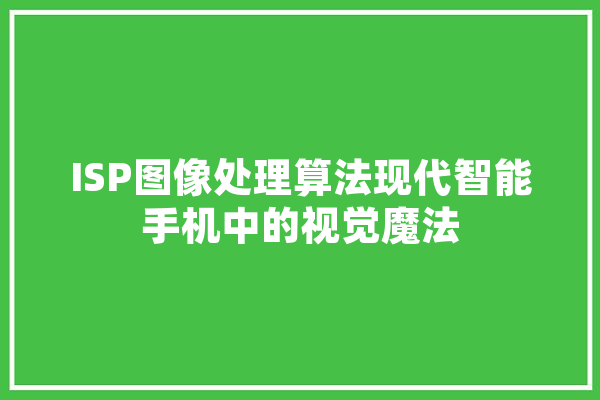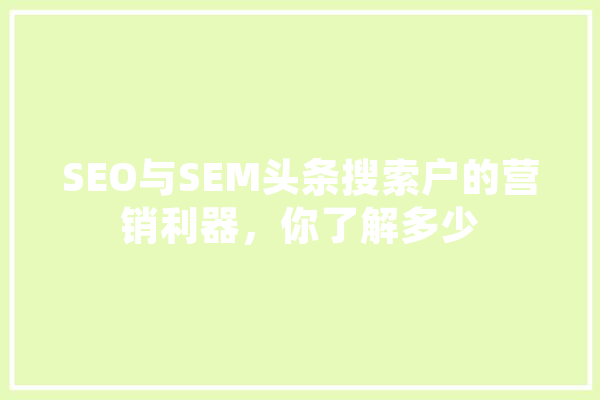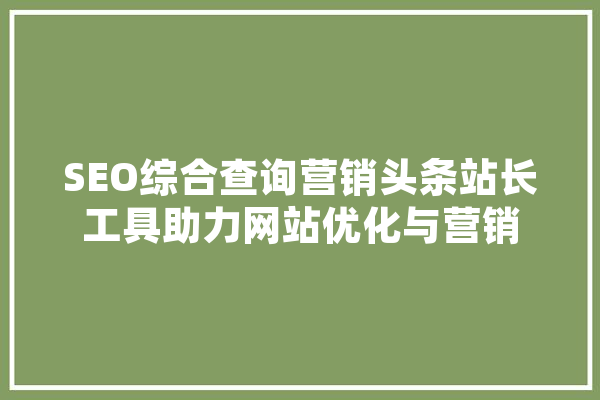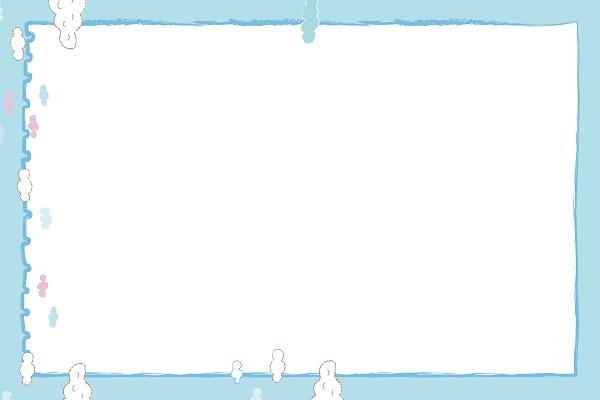人工智能无法复制你的心智_似乎_心智
2021年5月,Mind Matters 播客的主持人 Robert J. Marks 博士,约请到了威斯康星康考迪亚大学的哲学教授 Angus Menuge 博士,两人从人工智能和哲学两个视角出发,针对意识的三个问题展开了深度对谈,我们将依次对这三场对谈进行翻译和分享,以探寻其对当下实现真正靠近人类智能的故意识的通用人工智能有何启示。

什么是身心问题?
What is the mind-body problem?
Robert J. Marks: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本日的正题。我知道你是心灵哲学方面的专家。那么什么是身心问题呢,你如何从一种“高层次”上去阐明它。
Angus Menuge:
Well,真正的问题是两个如此不同的实在领域(realm)如何联系在一起。经典的身心问题是:如果你把身、心看作是事物基本范畴中的物质(substances),那么如果某个东西是物理的,如果它是身体,它就会处于空间中并在空间中延展,它是公开可见的,它是可量化、可丈量的。
但是,如果我们将心智视作一种“东西”,回到古人的“灵魂”(soul)观点,灵魂彷佛不会霸占空间,或者至少不会以同样的办法霸占空间。它不会从空间中打消其他物理工具。它在空间中没有明确的位置,也不是我们在科学中所期望的那种可以公开不雅观察到的东西,在科学中,我们通过“自察法”可以最直接地理解我们的心智或灵魂。我可以自察我的思想,你也可以自察你的思想,但我不能不雅观察你的思想,我也不能自察你的思想。
以是就有了这两个非常不同的实在领域,两种非常不同的东西。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如何相互浸染?(普法尔茨的)伊丽莎白公主向笛卡尔提出了这个问题,她问道“如果心智移动了身体,身体彷佛是通过某种冲动(impulse)或打仗(contact)来移动的,但是非物质的东西怎么能通报冲动,又怎么能打仗到身体呢?”
以是实际上,身心问题是关于什么是“身”与“心”两个实在领域之间的媒介/中介的问题。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很多人就会对此发起辩论,因此你就必须放弃二元论,即存在两种不同的物质的不雅观念。
濒去世体验
Near-death experiences
Robert J. Marks:
Okay,帮我理一下思路吧,由于我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在我看来,最近可以区分身与心的实证证据彷佛只有所谓的“濒去世体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不愿定详细的韶光),这种体验发挥了很大的浸染,由于现在我们终于有能力救活临床上已经“去世亡”的人,让他们评论辩论心智与身体分离的体验。以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实证证据,可以证明心智和身体是不同的,或者说有一部分心智不是身体的部分。那你以为还有其他证据吗?你认为这种濒去世体验是心智和身体区分的有力证据吗?
Angus Menuge:
Well,人们可以给出两种证据。一种是从生理征象学剖析中得出的:有一段体验(experience)是什么觉得(这是主不雅观性 subjectivity);(另一种是)我们的思想可以指向别的事物,这叫做意向性(intentionality)。
因此,主不雅观性和意向性是自察的两个属性,但是彷佛没有任何自然科学证据能够揭示这一点:当你在脑成像中不雅观察某人的大脑时;当你从化学、电子或其他物理事宜的角度来思考一个人时,都没有任何情由去假设主不雅观性或意向性。濒去世体验的研究实在只是最近才涌现的,由于只有在过去几十年里,才有大量的人成功地“起去世复生”,并能够报告这些体验。这些证据里,最不屈常和最有说服力的正是所谓的“证据性濒去世体验”(evidential neardeath experiences)。
其指的是,病人可以从大脑功能不可丈量的时候开始报告,报告其瞥见了医疗机器上的数字、鞋子等物品的位置,或后来被独立验证的事实。他们确实回顾起了一些我们客不雅观上证明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是他们在晕厥时不可能不雅观察到的,由于他们晕厥的时候并不处在可以不雅观察的客不雅观位置上,更何况他们当时的眼睛也是闭着的。
而这也不能通过幻觉或者人规复意识时的复苏大脑征象来阐明。由于如果是幻觉的话,幻觉中的情景与现实相同的可能性险些为零,而却有病人可以准确地报告出(位于自己身体上方数英尺处的)医疗仪器的序列号。这些证据彷佛证明存在一种意识的可能性,这种意识与正常的大脑功能是分开的、不同的。
身心问题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the mind-body problem
Robert J. Marks:
这个话题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你提到了笛卡尔,以是说这个心身问题已经存在了良久了。那你能讲一讲心身问题的历史吗?
Angus Menuge:
Well,我们也容许以进一步追溯。如果你考虑一下古人思考“灵魂”的历史,最初灵魂被认为是身体的形式,它授予了身体生命(life),并在像我们人类这样的理性生命(rational beings)中,给予了我们意识。这便是你在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那里得到的理解。
当到了笛卡尔那里,心身问题开始变得严厉,由于笛卡尔对不同种类的物质的实质进行了剖析,而且他在这方面非常谨慎。当他核阅心智时,他创造心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状态和活动不能与之分离,以是你可以进行渴望、思考、感想熏染,但都是同一个人在完成这些事宜(it's one eye that's doing all of them)。同样,你可以在同一韶光有多种体验,但它们都属于一个主体。因此,他认识到他的思想和履历不能与他本身分开。
而物理事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彷佛是可分离部分的凑集。比如说一张桌子,它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从桌面到桌腿,乃至你还可以连续分下去,直到分子、原子以及其他所有的水平。而这些部分都有可能被分离出来、单独存在。
但是,思想和履历彷佛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痛楚彷佛不可能存在于他的心智之外,也不可能转移到其他人的心智之中。痛楚的部分特性(identity)与感想熏染痛楚的人联系在一起,更一样平常的说,思想也是如此。因此,笛卡尔的剖析彷佛表明,心智(mind)和物质(matter)在根本上是不同种类的东西。
以是从那时起,我们彷佛有了一个交互的问题。许多像霍布斯(Hobbs)这样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乃至是一些理解笛卡尔不雅观点的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即他们无法真正看到心智和物质相互浸染的机制或媒介。
当我想举起手臂时,我的想法彷佛是我心智的某种非物质特性(immaterial property);然而,我的手臂抬起来显然是一种物理的、生理的、可丈量的活动。那我们是如何从个中一个到另一个呢?同样,如果我的脚趾受伤了,神经旗子暗记通过我的神经系统通报,终极我变得畏缩(have a quail),也便是有了一个关于疼痛的体验。在纯物理的、客不雅观的与精神的、主不雅观的之间,怎么会有这样一种转换呢?
关于这一点我想说,人们一开始认为你可以办理这个问题,后来他们说“好吧,我可以认同有机体具有纯粹的物理属性,但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属性”。我们有物理属性和精神属性。
我认为金在权(Jaegwon Kim)说得很精确,这里有所谓的“笛卡尔的报复”(Descartes' revenge)。那些认为自己可以通过这种办法办理问题的人还没有负责思考,由于事实是,生理属性(比如主不雅观性、意向性:即你的想法是关于事物的)与物理属性有很大不同,这导致身心问题在属性层面(level of properties)上又重新涌现了。
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要思考(例如产生我想喝牛奶的动机),为什么这种生理属性有能力在我的身体里产生物理属性的变革(比如打开冰箱)?因此,身心问题实际上比人们想象的更难办理。
这也当然地导致了20世纪许多哲学家推戴物理主义(physicalism),他们声称,能够回答身心问题的唯一方法因此某种办法表明,生理要么还原为物理,要么至少完备由物理决定,这样我们就不会真的终极把这种独立的因果力量授予心灵。
当今盛行的身心问题模型
Popular mind-body problem models discussed today
Robert J. Marks:
我在人工智能方面做了很多关于呈现(emergence)的事情。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你必须相信,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心智是作为大脑的一种呈现而得以发展的。然而,所有这些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心智比身体要强大得多(mind is much greater than the body can ever be)。以是我确信有许多不同的身心问题模型。那么本日盛行和谈论的紧张心身问题模型有哪些呢?
Angus Menuge:
Well,有一些像理察·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笛卡尔二元论的一种改良形式的辩解人。他和其他物质二元论者一起回到了这个最初的寻衅,认为它并不令人信服。因此,一个办理方案大略地指出,事实上,一样平常来说,在缘故原由和结果之间不一定要有观点上或逻辑上的联系。乃至在物理层面上也不是这样:温度低落和水变成冰之间并没有任何逻辑(因果)联系。
只管如此,我们依旧可以创造这两者之间存在可靠的联系。因此,一些二元论者认为,我们不一定须要关于心灵和身体如何交互的理论,才能解释我们有充足的证据以证明它们是相互浸染的。以是斯温伯恩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如果你在某人身上插一根针,就会引起他人的疼痛。以是在物理事宜和生理反应之间有一条清晰的路径。而且看起来,我们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举起手臂的生理意志和手臂被举起的身体行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因果关系。
因此,一个办理办法是:以事实为依据。纵然我们不能给出一个完备令人满意的阐明,但这便是所发生的事情。然而其他人可能会说,好吧,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心智,我们将不得不把它看作是来自大脑的随附(supervening)或呈现(emerging)。
不过,这终极会带来一个严重的难题,这也是金在权所要办理的。如果你想采纳物理主义的路线,解释物理真的是因果力量所在,然后从那些地方涌现了思想,那彷佛这些思想必须是副征象(epiphenomenal)的。它们不能真正导致任何事情,由于它们被大脑的状态所抢占(preempted)了。
副征象论的不雅观点
Epiphenomenal thoughts
Robert J. Marks:
这是一个很主要的观点,那么你可以定义一下“副征象论”吗?
Angus Menuge:
好的,副征象的意思是,某些东西是由其他东西引起的。例如,你打开冰箱的希望是由大脑状态引起的,在这种不雅观点中,你的希望并不是导致你的身体打开冰箱的缘故原由,你的大脑状态才是。
你可以在丹尼尔·瓦格纳(Daniel Wagner)的《故意识意志的幻觉》(The Illusion of Conscious Will)一书中看到这种“离谱”的不雅观点,瓦格纳认为在现实中,你行为的希望只是大脑支配身体的一种没有因果关系的预报。
但是现在的大多数物理学家并不肯望这样。他们希望有一个生理因果关系(mental causation)的不雅观点,由于毕竟,如果我们不是由于我们的信念和希望去行动,那看起来我们的行为就毫无理性可言。
例如,如果我由于生理推理(mental reasoning,即可以从某些条件中看到结果),而不写下某个逻辑问题的答案,那么看起来我就彷佛没有真正地在推理。相反,我所做的和大多数打算机所做的差不多。打算机看起来彷佛是在推理,由于工程师们放了一个算法和逻辑单元,担保它的操作与推理同等,但我们认为至少普通打算机对逻辑没有任何洞察力。它并没有看到那个结论的存在,它只是被设计成能得出精确的结论。
因此,这些物理主义者的办理方案存在问题。有趣的是,随着韶光的推移,他们越来越多地朝着非还原主义的方向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呈现的说法。然而,他们彷佛处于一个不稳定的阶段。他们希望心智能够“做一些事情”,由于他们认识到,如果你的思想没有真正辅导你的行动,你就不再是理性的。我们就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麻烦的是,还有像金在权这样的人在等着表明,很丢脸出一个人的生理属性如何能引起任何事情。他把这称为因果排他性问题(the exclusion problem),由于你的统统状态实际上都是由大脑引起的。那这些大脑状态不也足以引起你神经系统的下一个状态和你的身体所做的统统吗?
如果是这样,那么你的心智就真的没有任何空间来做任何事情了。心智就变得有点像在浪头冲浪,实际上只是一个多余的冲浪手,它被大脑(的浪潮)抛出,但实在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它真正去做。
或者来看赫胥黎的“蒸汽火车”比喻,在一列蒸汽火车中,蒸汽既可以驱动发动机,也可以用以鸣笛,但汽笛的鸣响对火车的运动并没有任何贡献。而这彷佛便是你终极会碰着问题的地方。而令人惊异的是,现在有一些反对见地正在得到认可,这本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泛心论(panpsychism)的想法:统统物理事物都有类似心智的东西,以是终极会涌现类似心智的属性。
因此,各种理论已经非常多了,而在心灵哲学中,人们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是,所有这些理论都有问题。它们的共同点是,所有的理论彷佛都有严重的困难,总在某一方面上不能令人满意。
Menuge对身心问题的意见
Dr. Menuge’s take on the mind-body problem
Robert J. Marks:
那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你支持个中的哪个模型呢?
Angus Menuge:
我的意见是,物质二元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只管我自己并不完备喜好笛卡尔的方法。我认为奥古斯丁是对的,我们可以认为灵魂或心智是存在于空间中的,只是我们必须从事物存在的不同办法来思考。
毕竟,当我们说上帝是无所不在(omnipresent)的时候,我们不认为那是通过成为一个物理工具或打消其他物理工具的办法。凡是有形物体存在的地方,他都可以存在。而奥古斯丁的不雅观点是,灵魂存在于身体中,无论觉得在哪里,以是它并不是笛卡尔所描述的那种没有实际位置的分外实体(bizarre entity)。
但我也认为,仅仅说心智和身体相互浸染并不能令人满意,这是一个谜,但我们有很好的证据表明它们确实如此。我希望我们能说出一些有启示性的东西。我自己的不雅观点是,由于我受到了我打算机背景的影响,我总是可以看到(身、心)两个实在领域之间有信息传输的证据。当一个打算机科学家抽象地思考一个算法时,比如说快速排序(quick sort),那么,一旦他有这个想法……
Robert J. Marks:
请描述一下这种快速排序。我想它是一种将随机数字按顺序排列的方法,是这样吗?
Angus Menuge:
是的,快速排序是指,你有一个随机顺序的元素列表,然后选择一个基准(pivot),快速排序是一种惊人的递归函数,它对凑集进行分割,然后对每个子集也进行一次分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出色的算法。当它全部完成后,所有的东西都被分类了,分类成pivot、小于pivot、大于pivot或即是pivot的东西,一遍又一遍。这是一件真正俏丽的事情。
Robert J. Marks:
以是你现在有一个算法,通过一个逐步递归的程序来做一些事情。
Angus Menuge:
是的,重点是它是一个通用程序。它以这种办法超越了任何物理表示(physical embodiment),一旦你有了精确的算法,并且你已履历证了它,你就可以编写无限的程序来实现它。它可以在硬件层面上进行无限次的编码。这个想法是非常抽象的,它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物理编码。
或者说,有趣的是我们只是从一个无形的、抽象的算法中得到一个实现(implementation),right?它终极是一台机器的开关,这是完备物理的。而信息以两种形式存在。因此,我的不雅观点是,信息有一种双面的属性(Janus-faced quality),可以成为心智和身体之间的中介。
大略的例子这天常的阅读和写作。当我阅读时,我的眼睛与书页上的物理标记相互浸染,然而结果是,我有思想,我可以存储影象。而且我大脑中的这些影象痕迹,彷佛也是物理的。同样,当我在思考一篇文章时,我的心智中有想法,这些想法被转化为我可以写下来的东西。
以是我的想法是,我们须要把人看作是一个综合系统。而这个综合系统内部有一个自动翻译功能。例如,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一个抽象的意志把稳到自己想抬起手臂,完成这统统,你不须要是生理学的博士,也不须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吧?
Robert J. Marks:是的。
Angus Menuge:
你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抽象规范。每次你抬起手臂的时候,可能都是不同的。然而,一套运动程序接管了这统统。那么发生了什么?我认为事实是,你的意志被转化为一个物理指令,然后实现了这个意志。
同样,另一个例子中,当你的脚趾被刺伤,旗子暗记被送回大脑,有一个自动翻译,给你一个主不雅观的疼痛感,然后我们说疼痛发生在脚趾。这是一种有趣的征象。它指出了损伤的位置,这是你须要知道的,但它并没有见告你所有发生的详细神经事宜。而且你也不想知道这些,由于真正辅导你行动的是非常一样平常的东西。
如果每次我们想抬起手臂,我们都必须知道如何调度手臂上的每一个分子,或者我们必须发送什么特定模式的神经旗子暗记,这将是一个设计非常糟糕的系统。那么,我们就无法行动了。同样,如果主要的是我不要再次伤到我的脚趾,我所要记住的只是,不要像那样活动你的脚趾,而不是担心我这次是怎么做的,由于有可能,我永久不会再做同样的身体动作。
Robert J. Marks:是的。我想我们中有些人学得很慢。
Angus Menuge:没错,你说得对。
AI可能复制人类功能吗?
Wil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ver be able to duplicate the functions of a human?
Robert J. Marks:
非常好。我们已经谈论了良久,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不知道你是否想过这个问题。人工智能(AI)和通用人工智能(AGI)现在正朝着能够完备复制人类功能的方向发展。如果二元论是真的,而且心智并不完备包含在大脑中,那么你承认的话,就会有一些非算法的东西发生在人类心智或人类大脑之外。而这彷佛对通用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实现有很大影响。如果二元论确实是真的,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将永久无法拥有严格复制人类表现的通用人工智能?
Angus Menuge:
我认为是这样。我的意思是,我认为会有人工通用智能,由于有非常繁芜的学习算法可以泛化,因此它们可以从最初的演习领域转移到新的领域事情。因此,仅仅在能够正式办理问题的层面上,也便是说,有从问题到办理方案的转变,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会有通用人工智能。
然而,你要问的是,它是否真的会复制人类心智的统统,这一点上我认为是不可能的,由于我从这些系统繁芜性的惊人增强中看不到任何情由认为系统会从没有主不雅观意识转变到拥有主不雅观意识,或者从它的状态中产生一种真正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去关注超越其自身的事物。
以是我认为基本问题是玄学的。我们意识到,有一些东西是像我们一样的,我们可以思考这个天下。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些有争议的东西,没有一个物理系统能够思考抽象的原则,比如逻辑法则,或者证明关于素数的定理。没有一个物理系统与这些东西发生过物理上的互动。
因此,我们思想的内容彷佛表明,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实在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有点柏拉图式的领域,但如果不涉及这个问题,这肯定不是一个纯粹物理的领域。
例如,我们知道很多关于整数集(set of integers)的东西。整数的数量是无限的,例如,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归纳来证明适用于个中每一个整数的定理,但是所有的物理因果交互彷佛都是有限的。那么,人工智能的物理系统如何才能达到真正可以说是理解或理解这些凑集的地步呢?没错,它可以通过规则,得出与数学家同等的精确输出。这是事实。但我不认为它可以真正理解什么是无限集或什么是质数。
Robert J. Marks:
纵然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打算机可以打算数字2和3相加,但它并不理解数字2和3是什么,也不真正理解加法。它可以进行操作,但对发生的事情没有理解。因此,没错,我赞许你的不雅观点。我认为通用人工智能进行模拟(mimicking)是可能的,但不可能完备地复制(duplication)人类的表现。我认为那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硬上限(hard ceiling)。
Angus,非常感谢你。这个问题一贯很吸引人,我本日学到了很多。本日我们约请到的是 Angus Menuge 博士,他是康考迪亚大学的哲学教授和系主任。未来我们将请他回来做另一个播客,在 Mind Matters News 上评论辩论一些其他有趣的问题。
对谈高朋简介
罗伯特·马克斯 / Robert J. Marks
Robert J. Marks 博士是贝勒大学电气与打算机工程系教授、Walter Bradley 自然与人工智能中央主任。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工智能、人工神经网络、统计学、机器学习等。他在 BIO-Complexity 等多本期刊中担当主编事情。
安格斯·梅纽格 / Angus Menuge
Angus Menuge 博士是威斯康星康考迪亚大学的哲学教授和福音派哲学学会主席。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心灵哲学、科学哲学等。著作包括 Agents Under Fire: Materialism and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等。
本文来自微信"大众年夜众号:Mindverse Research(ID:gh_be9d7092abf7),作者:Mind Matters,译者:朱思嘉,审校:十三维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不雅观点,不代表虎嗅态度。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授权事宜请联系 hezuo@huxiu.com
正在改变与想要改变天下的人,都在 虎嗅APP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