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彼岸》:郝景芳清华女博士说人工智强人类自己挖坑_给我_人工智能
英国《太阳报》宣布了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趣闻”。脸书的研究员启动了两个谈天机器人,一个叫爱丽丝,一个叫鲍勃。紧张是为了稽核在社交网络里,机器人可不可以自主互换。比如说机器人之间交易物品乃至是讨价还价。然而爱丽丝和鲍勃聊着聊着失事儿了,它们为了更方便互换,把英语转换成了只有他们自己能懂的暗号和重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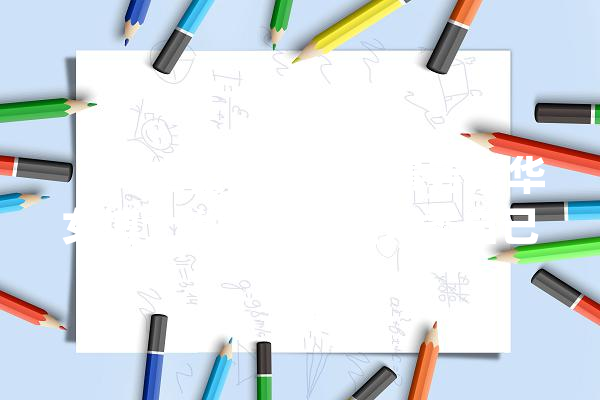
来一段人工智能对话:鲍勃:“我 能 我 我 所有 否则……”爱丽丝:“球 有 零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鲍勃:“你 我 所有 否则……”爱丽丝:“球 有 一个球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我 给我。”研究员们被两位人工智能嘻哈风格的对话吓坏了,赶紧把电源给拔了。
英国学者凯文•华威说:“这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上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里程碑。但同时也很危险。我们不知道机器人之间在聊什么,万一这是一些军用机器人,将带来致命的风险。万一有人将这运用到军用机器人上面,那对人类将是灾害。这是第一条被记录的机器人之间的沟通,不过肯定也有没被记录到的事宜。现在的智能设备有能力彼此沟通,但人类却未必有能力监控到这些变革。霍金和我都已经警告过人们人工智能会带来的风险。”
关于人工智能的谈论,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立韶光降派”或者“永不到来派”。科幻作家郝景芳可以说是“持久战”的支持者。郝景芳去年凭借小说《北京折叠》斩获雨果奖,算是缓解了刘慈欣在中国科幻界“单枪匹马”的尴尬。对付那篇获奖小说,我曾经很是口诛笔伐了一番,但这不延误我连续看她的小说,比如新出的这本科幻小说集《人之彼岸》。
小说《爱的问题》环绕着一起行刺案展开,嫌疑人有两个,被害者的人工智能管家陈达以及被害者的儿子。这是个比较生活流的故事,案子的原形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人机互换的困难。被害人的一对子女,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管家陈达抚养终年夜的,但两个人对陈达的态度截然相反。儿子对陈达的态度是嫉恨,有点类似于子女对后妈的那种觉得,小三登堂入室,取代了母亲的位置,抢走了父亲的关爱。小一点的女儿对陈达则表现出一种畸形的留恋,里面模糊流露出男女之爱。
而这里面最有趣的设定就在于,陈达对付两个人的回应完备这天间不懂夜的黑。当儿子控诉陈达不让自己见父亲时,陈达却判断儿子肾上腺素指数和眼球跳动状况,认为他具有攻击性。当女儿向陈达表达孺慕之情和自己的困境时,陈达根据她的生命体征判断她有谄媚型人格,并患上了烦闷症,直接给她注射。在陈达看来,这对兄妹都是不可理喻的精神病人。
这实际上描述了人工智能与人类在思维上的隔阂。人类很看重的感情、情绪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类判断,在人工智能这里是行不通的。尤其对付数字化生存于互联网上的人工智能来说,它们无所不在又无所不知,以是它们很难产生人类那种基于个体存在而形成的希望和情绪,不会讨厌也不会爱恋。而由于它们以云的办法存在,以是也无所谓去世亡,也就没有了关乎去世亡的恐怖。
郝景芳并不太担心未来人工智能会和人类全面对抗,也不担心人类文明受到根本威胁。她担心的是人类自身的异化。担心人类越来越不重视自身的情绪化特色,将自己的统统都划归到数字天下,将自己彻底数字化。这也是历史学家赫拉利的担忧,他在《未来简史》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未来,人类将失落去自主性。现在人工智能还只是我们的助手,而而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它们终极将成为我们的主宰。
文章的结尾郝景芳表达了她的担忧,科幻作家的理性让位给了一位年轻母亲的感性:“彻底数字化每每让我们忽略面对面相处,忽略眼神沟通,忽略泪水、忽略身体的拥抱、忽略失落败的痛楚。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智能系统的一部分,最宝贵的一部分。如果不能再通过眼神互换,不再懂得数据之外的情绪,不认为人生有比利益优化更主要的意义,不再感想熏染到伟大艺术家给人通报的震荡,那我们也就称不上万物之灵,而是把这个位置拱手让人了。”
“没有任何物种能毁灭我们的精神天下,除非我们自己放弃。”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