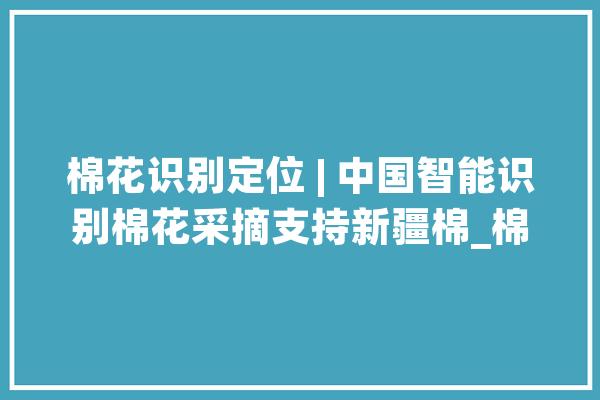河北农业大年夜学棉花遗传育种立异团队:5代人45年的“温暖事业”_棉花_团队
在河北农业大学,有这样一支传承5代的棉花遗传育种创新团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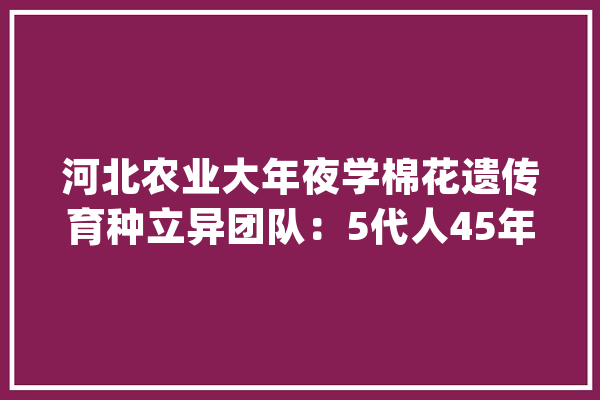
45年里,他们育成的28个不同特色棉花新品种,大多被列为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适宜棉区的主推品种,先后两次得到国家科学技能进步奖二等奖。
在基因组研究领域,他们的基因组设计育种干系研究成果,推动棉花育种从“海选”走向“定制”,还率先破译了海陆种间、陆陆种内基因组构造变异及其规律,为作物主要性状改良供应了新的理论依据和资源。
“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又到5月,正是棉花关键农时,随河北农业大学棉花遗传育种创新团队来到田间地头,近间隔感想熏染他们不懈追求的奇迹。
从“一个小目标”到28个新品种
2022年9月,马峙英(右三)和团队成员在位于新疆轮台的棉花育种试验基地查看棉花长势。 王省芬供图
5月2日,河北农业大学作物育种中央。
早上7时一过,8辆面包车驶来,“哗啦啦”下来50多名师生。接下来的两天里,他们要在中央的70多亩地里,播下造就出的6000多份棉花新材料。
劳碌的人群中,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师尤其引人瞩目。阳光照耀下,他的头发宛如绽放的棉花泛着银光。
他,便是河北省棉花育种首席专家马峙英,也是河北农业大学棉花遗传育种创新团队的带头人。
今年,是河北农业大学棉花遗传育种创新团队成立45周年。
“在这个团队里,我是从学生干起的,现在已经是团队里年事最大的了。”马峙英今年66岁,是规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当年的棉花产量,每亩只有三四十斤。”上大学前,马峙英在老家新乐就曾作为生产队副队长带领大家种棉花,对当时的棉花产量,他影象深刻。
棉花是主要的经济作物,“要发财,种棉花”,是当年马峙英在老家劳动时常听到的一句话。可枯萎病、棉铃虫等,却一贯困扰着棉花生产。
1983年,马峙英考取了河北农业大学研究生。他的导师曲健木,是当时公认的中国棉花育种专家。
1979年,曲健木教授牵头组建了以棉花抗病育种和良种繁育为固定研究方向的课题组,在我国较早地开始抗枯萎病育种、低酚棉育种及综合利用研究。这个课题组,便是河北农业大学棉花遗传育种创新团队的前身。师从曲健木后,马峙英正式成为团队一员。
“棉花育种,是‘衣被天下’的‘温暖奇迹’,一辈子造就出一个品种就不得明晰。”马峙英至今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导师曲健木曾这样告诫自己。
出品种,就这样成了马峙英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小目标”。
没想到,马峙英加入团队的当年,第一个“小目标”就实现了。
打响头炮的,正是曲健木带头育成的河北省第一个抗病、早熟、丰产品种——冀棉7号。
“在此之前,河北一贯没有自己的抗病品种,冀棉7号育成后,棉农再也不用害怕枯萎病造成的大面积去世苗了。”马峙英先容。
1979年至1992年,河北农业大学棉花育种课题组与石家庄地区农科所、邯郸地区农科所成立河北棉花抗病育种互助组,开展育种攻关研究。
冀棉7号面世后,互助组又相继育成了冀棉14、冀棉19、冀合372、冀无252等棉花新品种,同时根本理论研究也得到深入开展。这些品种和研究,使河北当时已成专横獗之势的棉花枯萎病得到了有效遏制。
1993年,曲健木教授离休后,马峙英正式成为团队带头人。
从年轻小伙儿到满头白发,马峙英亲历并见证了团队“逾额完成”当初那个“小目标”的全过程——45年里,团队先后育成了28个不同特色棉花新品种。
个中,马峙英带队育成25个棉花新品种,先后两次得到国家科学技能进步奖二等奖,农大棉7号、8号、9号被列为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重大项目,农大棉6号、9号、601分别被列为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操持、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抗虫杂交棉新品种育繁推及家当化、河北省当代农业家当技能体系重大成果转化项目。
这些品种均在冀、鲁、豫、晋、新等棉区大面积推广,“小目标”结出了“大棉桃”,种出了“大棉海”。
“有了这些品种,棉农们再也不用给棉花‘涮棵’、打药治虫了。”马峙英先容,以往农人在防治棉铃虫危害时,常常是用药水给棉花“沐浴”,俗称“涮棵”。药水对人体有害,常常有人中毒。因此,马峙英到屯子推广新品种时,常常被棉农问到如何有效防治棉花病虫害。
“现在,我们仍在研究新品种,从最初的抗病丰产,到后来的抗病虫高产优质,现在的育种方向是在抗病虫高产优质根本上,还要耐盐碱、早熟、适宜机采等。”
马峙英先容,近几年,团队又育成了冀农大23号、24号、36号等适于机采的早熟多抗优质新品种,目前已经广泛栽种,“储备的新品种,已经到冀农大47号、48号了。”
从育种2.0向4.0的迭代
5月20日,河北农大人工景象室,马峙英(左二)与团队成员查看棉花基因鉴定试验。 赵凌云摄
5月11日,跟随马峙英来到研究团队的一间人工景象室。
几十盆20多厘米高的棉花植株,在控温控湿的环境,悄悄绽放着新绿。这些棉花植株,全部由团队采取当下最前辈的生物育种方法造就而成。
“要育出好品种,我们总结的履历是,育种技能必须一贯走在最前沿。”马峙英先容,农业育种技能发展到目前,被分为4个阶段,简称为育种1.0、2.0、3.0、4.0阶段。
育种1.0阶段即为履历育种,依赖作物表型来选择自然变异。育种2.0阶段,最范例的便是杂交育种技能,但对其基因型仍不清楚。育种3.0阶段即为分子育种,如借助分子标记、转基因等手段,使植物得到抗病虫等关键性状。育种4.0阶段即为生物育种,要研发集身分子标记、基因编辑、全基因组选择、大数据剖析等技能。
1983年,马峙英加入团队时,正值育种2.0阶段,当时的他为了做试验,险些每天往地里跑。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便开始了育种3.0干系技能的考试测验。”马峙英先容。
抗黄萎病新品种,是河北农业大学棉花遗传育种创新团队的一项“成名作”。
事实上,这次育种的成功,正好离不开一项前沿的“3.0技能”的研发。
棉花黄萎病是植物土传病害中最严重的一类,病原菌侵染根系后会转移到植株维管束系统,传统喷药的办法无法杀去世病原菌。因此,黄萎病当时被称作棉花的“癌症”。20世纪90年代,棉花黄萎病在我国黄河流域大爆发,河北80%的棉田受到病害威胁。
经由对国内外干系情形的研究剖析,团队创造,造就和栽种抗病品种,仍旧是掌握该病害最根本、最有效的路子。
“抗病不高产,高产不抗病,一贯是育种事情中一对难以调和的抵牾。”团队成员、河北农大农学院博士生导师王省芬阐明,详细到抗黄萎病品种造就,空想的品种要实现抗病、丰产双赢。
带着这样的思考,大家的目光,投向了当时最前沿的育种技能——分子标记育种。
可当时,分子标记育种技能尚不成熟。为此,马峙英专门报考了华中农业大学读博深造,师从海内一流的棉花遗传育种学家孙济中教授。
为开展干系研究,团队不仅购置了打算机、离心机、基因扩增仪、电泳仪、超净台等高端研究设备,还专门到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向当时的业内威信学习请教。
“要进行分子标记育种,须要有足够的种质资源进行研究。我们光是到省内外网络的种质资源,就有2000多份,耗时两年多。”团队成员、河北农大生命学院研究员吴立强先容,在此根本上,团队又从河北37个产棉大县采集了大量黄萎病致病菌样本,才初步建立起了抗病种质资源库。
“我们这个资源库,虽然种类不是海内最多的,但却是以抗黄萎病为目的网络的,称得上是最有特色的。”吴立强说,团队还将常规的育种技能与新兴的分子标记方法相结合,研究创造了病菌的落叶型菌系和品种的抗病类型及分子标记,终极创新了抗黄萎病育种理论和方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8年,团队造就的“冀棉26号”和“农大94-7”两个抗病新品种同时通过审定。2004年,抗病杂交棉农大棉6号通过审定。
但马峙英仍不知足。“相对付弘大的棉花基因组信息来说,分子标记育种仍旧是零敲碎打。”马峙英表示,人们对棉花当代育成品种的基因组信息、当代育种过程中基因组的构造变异仍缺少深入理解,有关棉花构造变异的遗传效应鲜为人知。
于是,团队又在提高育种水平和效率的育种4.0技能高下起功夫。
伴随研究的深入,团队的基因组设计育种干系研究成果频出,不仅推动棉花育种从“海选”走向“定制”,还率先破译了海陆种间、陆陆种内基因组构造变异及其规律,为作物主要性状改良供应了新的理论依据和资源。
“到目前为止,全天下棉花基因组测序领域揭橥了17篇顶尖论文,中国学者打破性地贡献了15篇。”马峙英先容,个中,就包括以河北农业大学棉花遗传育种创新团队为主完成的2篇和团队参与完成的2篇。
“现在,我们对育种4.0技能的研究和运用仍在不断深化。”马峙英先容,团队目前正承担着一项国家级棉花生物育种项目。
5代人的传承
5月10日,河北大范围降雨,保定涌现了强对流景象。
“这种景象,特殊随意马虎有冰雹。”窗外***,团队成员、河北农大农学院博士生导师张艳的心揪得牢牢的,恐怕前几天刚种到地里的棉花材料出意外。
棉花苗期,最怕下冰雹。
两年前,便是由于一场冰雹,团队种在地里的试验材料,叶子都被砸掉了,险些变成了根根“筷子”。
“这些材料,很多都是这一代就要鉴定的,一旦被砸,当季就出不告终果了。”张艳阐明,最怕的是,这一代材料被“砸”没了,上一代也没保留住,就很难进行材料“追踪”了。
近年来,团队的育种一线事情中,张艳这样的青年科研骨干操心得越来越多。
“马老师一贯跟我们讲,搞农业就要‘顶天立地’,无论育种技能多么‘顶天’,育种人始终离不开‘立地’。”张艳阐明,所谓“立地”,便是要真正与作物“同风雨”“共命运”。
“最近我们参加博士生口试,险些每个人都提到自己特殊‘吃苦刻苦’。”
听到“95后”学生们这样的回答,身为博导的王省芬感到很欣慰。
“不论是育种技能,还是硬件条件,现在学生的科研环境好多了。但由于农业研究,特殊是棉花育种的分外性,科研中该吃的苦还是得吃。”王省芬说。
再过两个月,棉花就要进入着花结铃期,那是一年中景象最热的时候,也是团队得到表型数据和配置杂交组合的关键期间。
每年从7月15日到7月30日,整整半个月,团队都得“长”在棉花地里。“站在地里,就像站在蒸笼上一样,又热又闷,光晒就能把人晒得脱掉几层皮。”王省芬说。
但造诣感又是实实在在的。
今年53岁的王省芬,老家在石家庄市藁城区东部的兴安镇,从她记事儿起,当地就一贯种棉花。上大学之前,王省芬还总帮着母亲到地里捉棉铃虫,“虫子多得呀,捉一天,晚上回去恶心得吃不下饭。”
但随着棉花抗病抗虫育种技能的提高,当年的糟心体验早已不复存在。王省芬真切地从育种事情中感到科研的代价。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得到这么小一棵植株,至少得10个月。”在人工景象室,王省芬指着一棵约20厘米高的棉花植株说。
“从一棵小苗,两片叶子刚展开,就截一段茎开始培养,泡在带有目标新基因的菌液里,等这段茎长出愈伤组织,我们就要通过组织培养再生技能,从愈伤组织里找到胚状细胞进行造就。”王省芬先容,长成小苗后,他们还要一贯根据棉花苗的成长情形换培养基,越到后边换培养基的间隔越短,就像给婴儿调配奶粉一样。
培养苗,同样也在培养人。
培养一株苗,须要十个月,而培养一代人,少说要八九年。45年来,从曲健木到马峙英,从王省芬到张艳,再到“90后”新生代,团队至今已传承到第5代。
30岁的“海归”博士王星懿,是团队里最年轻的队员。
这样一个一贯在实验室里搞分子育种研究、从没下过大田的年轻人,能不能忍受农业科研的呆板和辛劳?起初,大家都有些担心。但一项棉花种子的顶土力试验,让大家打消了疑虑。
试验中,王星懿要把419份材料,分别埋在花盆的不同土壤深度,来测试材料种子萌发时的顶土力强弱。
试验统共设计了3个播深梯度——5厘米、6厘米和7厘米。也便是说,每一份材料,王星懿都要分别种在3个花盆里,进行比拟试验。完成一批试验,她就要播种1257个花盆。这样的试验统共要进行3批,每一个月做完一批。
事情量大,但并不是最难的。
“每个花盆要播下15粒种子,垂直分布上,土壤紧实程度要保持同等;水平分布上,种子还必须间隔均匀。”令王省芬感到惊喜的是,王星懿还专门做了个类似漏网的小赞助工具,轻轻松松便应对了这些“刁钻”的试验哀求。
既要有脚踏实地的劳动,又要有科学研究的聪慧——这是团队一起走来的关键支撑,也是团队一代代传承下去的稳定内核。
而这,也是马峙英带领团队一贯践行的“科学家精神”之所在。(河北日报 周聪聪)
关注河北***网,理解河北最新***。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