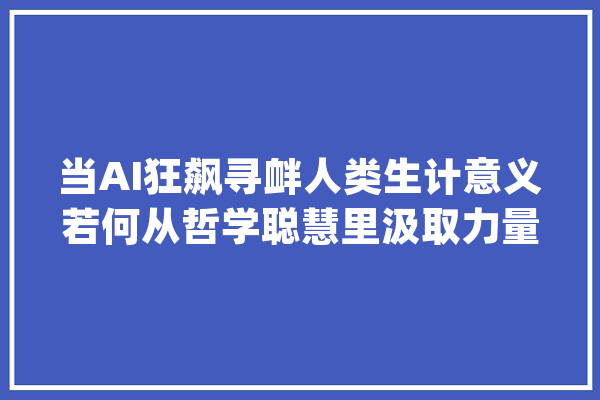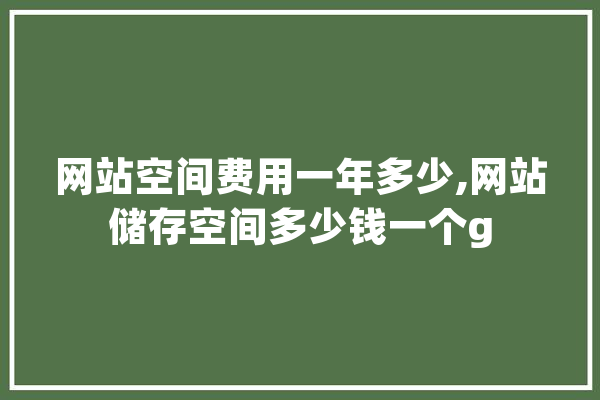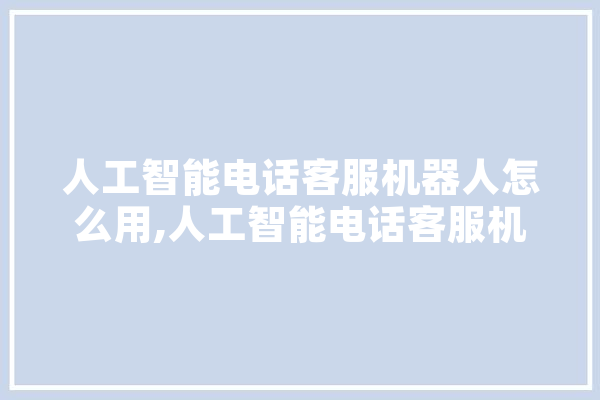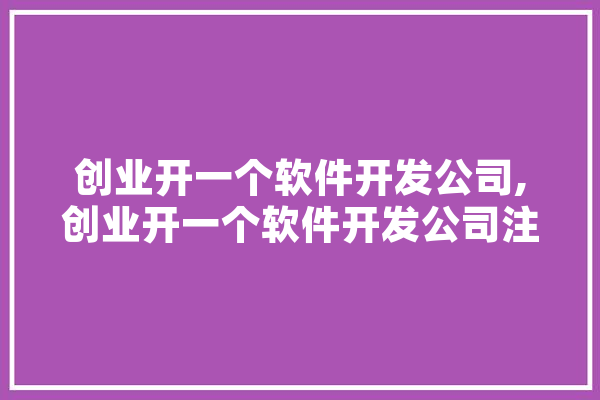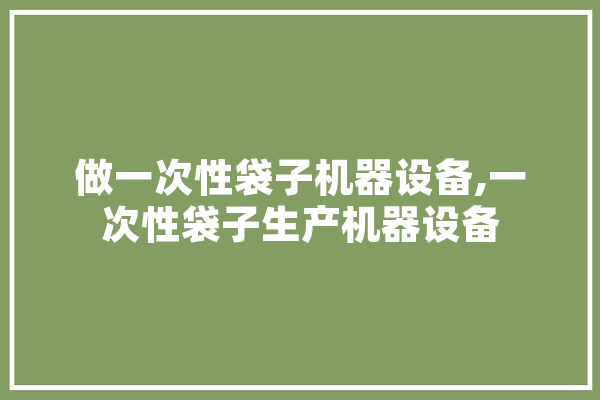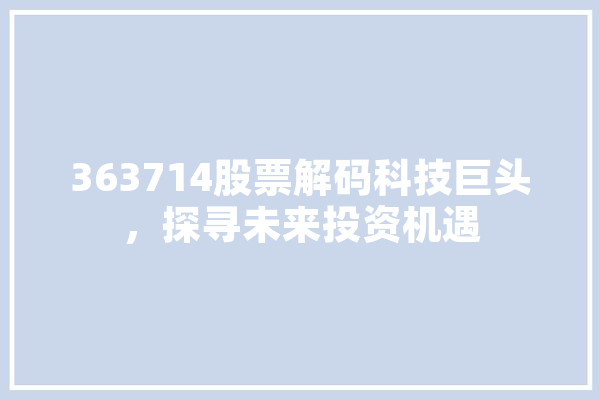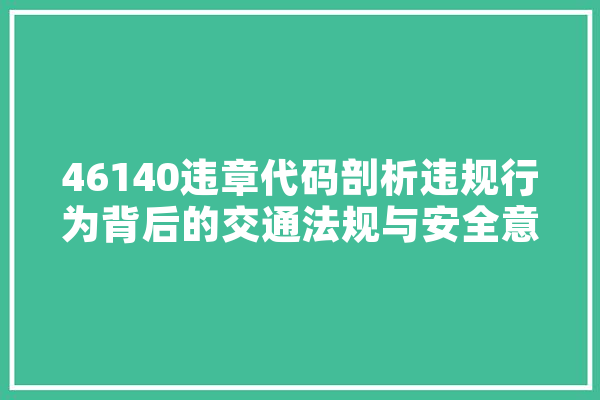行知读书会|加缪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存在主义危机_加缪_危机
7月27日,作家、文学译者俞冰夏做客由上海宝山区大场镇公民政府、阎华事情室、上海公民出版社市场部主理的行知读书会,讲述作甚“人类的危急”以及加缪的作答。同时,俞冰夏还谈论了人工智能时期的“存在主义危急”,并分享自己翻译长篇小说《无尽的玩笑》的心途经程。

俞冰夏
当人和机器的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时,当人们活在像素的天下里,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俞冰夏先容,在加缪的时期,所谓“存在主义危急”,在二战往后普遍存在,人们在重复性的事情当中看到极致的荒诞。加缪的结论,众所周知是“西西弗式”的。每个人或许便是西西弗,而西西弗也可以是幸福的。加缪虽书写绝望与挫折,也视生活为“幸福”,其作品乃至带有某种乐不雅观。
1946年,加缪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题为《人类的危急》演讲。俞冰夏分享了加缪美国之行的所见所闻,她从加缪日记中探求到这次演讲背后的故事,深入磋商了加缪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主题的演讲。
“加缪演讲中,希望把人从天下危急当中逃离出来,他首先从各方面阐明了荒诞性,即人类面对的危急:代价腐败引起的恐怖,没有一个人对将来有把握,即虚无主义的方向;‘人类危急根源在于人无法说服人’;自然被印刷物取代(如今,即算法使人变得伶仃);人变成政治的人,激情不再是私有的,而是集体的,因而是抽象的;对效率有一种抽象的崇拜,总是认为要做有效率的事情,对付做什么事情本身一点不关心的。但是,加缪仍旧想要找到生命的意义,鼓励大家从个人的角度,从极致追求自由的,打破自我的角度去追求人生的意义。”俞冰夏先容。
去年,俞冰夏翻译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作品《无尽的玩笑》出版,这部一百万字的小说被认为是天才之作。华莱士在其演讲《这便是水》中同样分享了关于“存在”的困惑。他见告青年人们步入社会即将面临的关于人生的原形,如加缪,同样是“西西弗式”。而后者乐意以那些西西弗式的日子是有幸福的、有希望的。
俞冰夏认为,当下的存在主义危急所面对的或许是“人工智能”。如果不相信西西弗是幸福的,那么终会相信人工智能会完备取代人。如果不相信做人具备崇高性或是幸福的,人工智能也会完备取代人,人没有必要存在。俞冰夏指出,人工智能与人类存在两点差异,第一个人工智能体会不到什么是“幸福”;第二人工智能也没有受过什么苦。
从加缪到人工智能时期下的“效率”问题,俞冰夏分享了她为什么会花费四五年韶光翻译这部鸿篇巨作《无尽的玩笑》。俞冰夏以为,20世纪后半叶,知识分子在小说创作中产生了一种玩弄形式的方向,用形式粉饰自己对真实情绪,感情和想法的渴望和抒发。多年以来,她一贯试图办理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在与自己的对话和狡辩中,脱身出来?《无尽的玩笑》给了她很多启示,各种辩证法度模范的思考方法。她提到,华莱士最喜好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看来,意义可能并不是繁芜而高尚的东西,而只是人与人之间大略的互爱,像伸出一只温暖的手。
“如果统统经由机器完成,我们存在的意义将更为危险。当人认为自己是可被取代的时候,或是人类最大的危急。因而加缪对当下依然存在主要的辅导意义——‘只要在聪慧和真理的道路上,只要存在这条道路,就不会有大略的捷径,天下上也没有任何大略的捷径。’加缪所希冀的正是人类危急下的希望,当下亦如是。”俞冰夏说。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