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文学的价值追问_人工智能_文学
人工智能在文学领域的实践虽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但引发学术界对其关注并热烈磋商,则是在以ChatGPT为代表的天生式人工智能涌现之后。从小冰、九歌、Botnik,再到ChatGPT天生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真正冲破了人类创造文学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且正在渗透至真人文学,乃至重新定义文学。传统的文学样式、创作办法、接管过程、传播路径等,均因此发生巨大的变革。确定人工智能文学代价的创造主体,剖析人工智能文学代价的内涵,追问其代价取向与文学意义所在,是精确认识与客不雅观评价人工智能文学的必要之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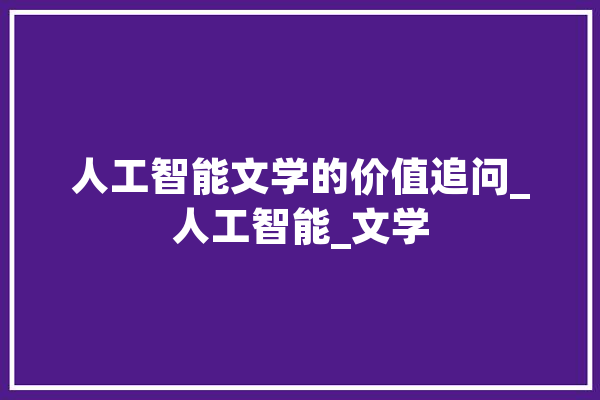
作为创造主体的人与机器
随着大措辞模型算法与算力的不断升级,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能力不断提升,天生的文学作品也越来越成熟。小冰已陆续出版了三本诗集,Botnik续写的《哈利·波特》被网友称为“读过的最好的作品”,小说家詹妮弗·莱普更是利用ChatGPT同时进行七部推理小说的写作。人工智能创作的文学作品被越来越多的读者阅读、接管和认可,其文学代价也逐渐得以显现。但须要认清的是,人机协同作为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根本,其文学代价也是由两者共同授予的,应客不雅观核阅人与机器在代价形成中的不同分工与浸染。
一方面,人类对人工智能文学的代价形成具有主导性的浸染,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无法离开人类而独立存在。作为数据创建者与指令发出者,人类的情绪方向、创作意图和代价不雅观念都会在算法与天生内容中表示。人工智能在海量数据的深度学习中,节制的是文学的写作老例与表达技巧,并不会像人类一样受精神须要的驱遣而产生创作冲动。人类作为人机关系中的主导者,其发出的指令是天生文学内容质量的决定性成分。这不仅仅须要人类用户具备一定的指令写作能力,还磨练其文学积累以及创新思维。从目前来看,较为完全与成熟的人工智能文学作品均须要人类用户对人工智能进行分阶段的指令性勾引以及多轮的人机互动,人的反馈见地是文学内容质量提升的主要驱动。
另一方面,机器学习作为人类思维的补充,是创造人工智能文学代价不可或缺的一环。“人机互助”的创作模式是人工智能文学差异于真人文学的一大特色。机器强大的信息搜索、归纳与整合能力作为人类创作思维的有机补充,填补了人类在信息搜索与影象等方面的短板。但人工智能文学内容的天生,不仅仅是对数据库的直接调取,还会通过概率与反馈对用户指令进行差异化的解读。因此,人工智能的文学“创作”有时会在用户积极勾引下,跳出人类逻辑与思维定势,天生新奇的文学内容,带来新鲜的阅读体验,使文学作品具备一定的审美代价和创新代价。随着人工智能文学作品的推陈出新,很多学者都认识到了“人类中央主义”作为人工智能文学评价标准的局限性。目前来看,人工智能还远远不能分开人类而成为新的创作主体。
在商业代价与精神代价之间
人工智能文学生产办法的独特性,使其文学代价的内涵差异于传统文学。首先,天生式人工智能是凭借全新算法与强大算力对海量人类文化内容的深度整合、混搭和模拟,其一键天生的文学作品所展现的是人类科技文明的最新成果。可以说,人工智能在技能上的每一次打破,都一定会为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能力带来巨大提升。例如,仿照人脑的人工神经网络使人工智能节制了人类自然措辞的概任性特色;基于预演习的深度学习使人工智能识得了各种文学类型的写作老例与表达技巧;强大算力使人工智能拥有了人类难以超越的天生速率;多模态信息技能对文本与图像的跨媒介打破,进一步引发了人工智能文学创作的广度与宽度;而创意对抗算法又使人工智能规避了公式化的风格方向。正是在上述核心技能的加持下,人工智能得到了可以“代理”人类进行部分内容创作的能力,与人类共同构成了艺术中的“行动者网络”,开始真正动摇人类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地位。
然而,也正是由于对技能的高度依赖,人工智能文学除了在诗歌上小有造诣外,更多集中于推理、侦查、科幻等类型化的普通小说和网络文学创作中。马库斯·杜·索托伊对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具有复苏的认识。他认为,“人类创建具有创造力的算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扩大艺术创作的希望,而是为了增加贩子们在银行的存款”。人工智能文学潜藏的巨大的商业代价在不可避免地将其引向大众化、娱乐化和庸俗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内容抄袭、信息造假及版权轇轕等问题的不断涌现,使许多文学创作平台和学术研究平台严禁AI的利用。
随着对人工智能天生机制的不断理解,人们对人工智能在文学等艺术领域的参与,开始从质疑、焦虑转为积极面对。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的互助伙伴,在提高人类写作效率、引发创作潜能等方面的前景无量。我们没有情由反对文学的商业代价,但是作为表达人类精神追求的措辞艺术,其精神代价是市场经济的砝码永久无法衡量的。
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的创作机制决定了其文学作品势必与人类顶级作家存在巨大差距,文学代价的核心内涵也使其更易受到成本与技能的掌握,从而导致机器文本的泛滥。与此同时,真人文学具备的人文代价与精神代价反而会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断被凸显和放大。因此,人类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必须考虑对社会、民族以及人类的崇高的任务感,以传达文学的人文代价和精神代价为己任。人类作为文学创造主体,要充分发挥主体性、能动性、目的性和创造精神,成为文学代价的引领者,而不是数据的依赖者、技能的跟随者。
以人文代价纠正算法偏见
人工智能的算法技能在无数次的数据演习中学会的不仅仅是人类自然措辞的通用规律,还有隐蔽在措辞背后的代价不雅观念。详细到人工智能文学的创作活动中,算法在反复的文学演习中,会将人类对付文学的一系列不雅观点与意见,以较为固定的形态呈现在模型运算中。作为一种认知活动,文学代价不雅观念一旦被文学活动主体所节制,它也就同时节制了文学活动主体,从而勾引、制约文学主体的创作、批评或阅读欣赏活动。算法一旦被人工智能所节制,也会掌控人工智能,从而勾引、制约其文学创作方向和文学代价的取向。
随着算法的遍及与运用,算法偏见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算法偏见作为一种“内生性偏见”,个中包含的爱憎、取舍、抑扬、褒贬,都会影响人工智能对人物形象、故事背景、场景描述、详细情节等文学材料的选择与组织,而代价不雅观念则会以表象—情绪的样态蕴潜在文学作品中,通过作品中所描写的、表现的生活形象的代价属性以及创作主体的评价态度呈现出来,从而影响读者的阅读与接管。此外,算法偏见也会涌如今文学批评中,影响人工智能文学乃至真人文学的评价标准。AI批评家的涌现,意味着算法带有的偏见与歧视,也会在人工智能进行文学批评活动时内化为文学作品的评判标准,进而对文学作品天生缺点的认知与评判。这不仅会殃及文学作品与作家本身,对付依赖网络数据、代价态度模糊的读者来说更是相称危险的存在。
算法偏见作为一种代价不雅观念偏见,会通过技能的更新迭代被放大与强化,从而造成人工智能文学代价取向偏离精确的方向。有学者针对算法偏见,倡导“代价算法”革命,以反拨既往的工具理性情局,拯救算法危急。而改变算法倾向的关键,则是作为算法利用者的人类本身。因此,在人工智能时期,人类进行文学创作时也必须凸显其人文温度、审美理性与批驳态度,发挥文学在伦理道德、教诲勾引、代价规范等方面的浸染,对文学活动的代价取向加以纠正与引领。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文学将会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对既有的文学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传统的文学代价不雅观念与文学评判标准均有可能失落效,须要我们对其进行重新思考与把握。虽然人工智能对未来文学的发展与文学生态的终极影响还未可知,但文学代价的引领者与规范者,必须是人类。而打破常规俗见,彰显人文精神,表示人的存在意义的,也必须是人类创作的文学作品。
(作者系山东艺术学院艺术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仅代表作者不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供应信息发布传播做事。
ID:jrtt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