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常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前瞻_人工智能_轨制
制度应对:积极容纳与谨慎颠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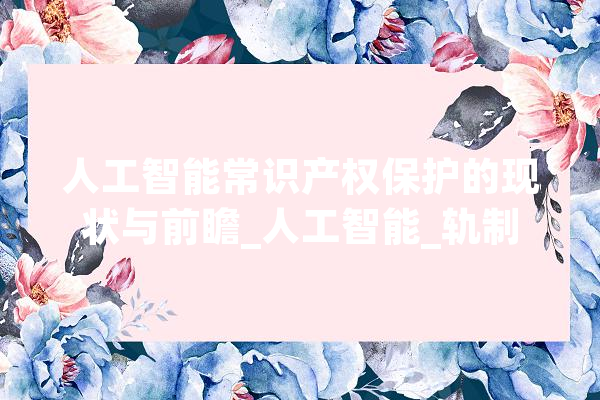
在对人工智能问题的诸多磋商中,不乏所谓“人工智能正在颠覆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哲学认知和制度标准”之类的说法。只管“未来已来”的人工智能确实正在产生新的保护客体(如数据产品),创造新的保护领域(如算法的竞争法调度问题),以及带来保护标准的适应(如算法的专利授权标准),但大略断言人工智能对付知识产权制度形成颠覆还为时尚早。
历史地看,知识产权制度历经300余年,总是不断受到新科技和新家当的冲击,虽在制度上不断完善和理念上不断更新,但基本体系是相对稳定、稳步变革的,改造和变革更多是在保持基本体系稳定的条件下逐步完成,而不是动辄发生颠覆性改变。例如,版权制度产生于传统的手工制书时期,后来随着印刷和传播技能的发展屡受冲击,使得版权制度不断扩容,不断增设新内容和拓展新边界,但新的拓展都是在原制度的根本之上,常日不轻易颠覆根本性制度。再如,印刷术的产生催生了复制权;广播电视技能的发展催生了传播权;互联网技能使版权保护从纸质时期进入数字时期,催生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等等。但是,每一次制度创新都是在原制度之上的变革、扩展和丰富。只是经由相称长的历史期间进行回望时,屡经阶段性变革的法律制度与最初比较可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而这种变革正好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累积形成的。
有人认为,人工智能的涌现不同于以往任何技能对付知识产权制度的冲击。这种断言为时尚早。只管机器人、智能创作、算法、大数据等新观点新术语令人眼花缭乱,但现有法律体系具有足够的容纳力,对新客体进行审时度势的调度。法律实践中已经涌现的数据产品案、人工智能天生物著作权案等涉人工智能案,都采纳了此类裁判态度。
概括而言,涉及人工智能的冲击与办理的环境有以下几种:其一,现有制度的自然涵盖。如算法的专利保护,无非是在现有专利授权标准之下,根据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的需求,划分出可付与专利的“技能方案”和不具有可专利性的“智力规则”。利用人工智能创作的作品,基本上仍旧纳入现行著作权主体和客体进行衡量。数据产品已纳入民法总则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度。其二,在发展中谨慎应对。例如,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产品涉及的利益关系繁芜,民法总则尚未直接将其定位为民事权利,但实践中已产生保护的需求,当前的法律充分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权利孵化器”的浸染,先肯定数据产品为受保护的法益,并依法给予保护。数据产品能否和如何上升为权利,仍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其三,在现有制度之外开辟新领域。即在上述路径不能容纳时进行制度创设,这种环境多少有些颠覆性。总之,对付人工智能带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新问题,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应对的基本态度是积极容纳、谨慎颠覆。
科技创新与家当发展:制度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架构和设计一定服从于和做事于创新与发展的现实需求。实践中,当知识产权法律规则适应科技创新和家当发展需求时,法律规则具有规范其发展的功能;反之,科技创新和家当发展一定以各种办法打破现有制度藩篱,终极建立新的适应性制度,实现制度规则的除旧布新。可见,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应充分表示科技创新和家当发展的需求,为创新和发展创造空间。例如,在信息高速公路和互联网兴起之初,美国克林顿政府曾发布绿皮书,试图沿着着重强化版权保护的旧轨道和原思路,呼吁在互联网环境下着重加强版权保护。但是,互联网环境迎来了权利人、网络做事供应者和社会"大众年夜众的新利益格局,尤其是科技创新和家当利益的保护受到突出关注。在新旧各方利益博弈之下出台的数字千年版权法创设了避风港、红旗标准、关照删除规则等新的制度设计。这些新的制度设计,显然不是从已有法理推论而来,而是立法者依据现实情形的变革,综合考虑科技创新和家当发展须要作出的法律回应。同样,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必须充分考虑科技创新和家当发展的需求。
知识产权具有独特的利益平衡机制,其最根本的利益平衡是权利保护与公有领域的比例关系,即以最大化创新勉励为公约数,合理确定权利保护的边界和强度,留下必要的公共空间,以确保创新的可持续性。例如,软件发展初期,20世纪70年代美国曾经就软件能否纳入版权保护进行过谈论,为办理该问题美国国会还专门成立“版权作品新技能利用国家委员会”,提出了采纳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将打算机程序视为笔墨作品进行保护的研究报告。打算机软件中的措辞表达显然迥异于传统的笔墨作品,美国将打算机软件作为笔墨作品进行版权保护,显然紧张不是由传统版权法理推论而来,而是紧张考虑到,补充对打算机软件进行版权保护的法律空缺,有助于促进打算机技能和软件家当发展。此后,这种做法被写进了WTO项下的TRIPs协定。在本日,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知识产权保护新议题,在确定是否以及如何保护的态度时,立法者的利益平衡考量也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家当发展为条件。例如,人工智能创作物的可版权性问题情形繁芜,有的创作物存在较多的人的干预成分,有的则更多是人工智能本身创作的。以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的创作物,其可版权性更适宜以现有的法律标准进行衡量。但对付人工智能独自完成的创作物的可版权性问题,应该以更好地处理权利保护与公有领域的关系,以及如何更有利于勉励创新和促进家当发展的须要,决定是否保护和如何保护。如果将纯属人工智能创作物的“作品”纳入公有领域更利于创新和发展,可以否定其可版权性;否则,可以进行保护。
现阶段,人工智能科技和家当涉及的知识产权保护仍紧张是在现有制度体系内完成,更多是办理现有制度如何适应和适用问题。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首先是纳入和兼容,在无法纳入和兼容时进行零散的或者局部的创新和打破,对付现有制度的革命性颠覆很少发生。总之,既不能守旧和墨守成规,又不能盲目冒进,而必须以需求为根本和实事求是。该打破时绝不犹豫打破,无需打破和颠覆时仍应进行兼容性和调适性适用。
实现自然人利益: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
人工智能是对付当今更具有人或者超人色彩的智能科技发展阶段、技能、产物和趋向的一种定义和表达,但无论如何,其毕竟是人类科技发展的一个阶段、过程和趋向,是人类主导之下的一种科技进步和造诣。无论当前对付人工智能的“智力”和“创造力”有多么新鲜和惊人的描述与预测,无论人工智能的前景是胆怯还是诱人,人工智能的知识产权保护都须要以人为核心。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设计中,应该以人的需求为主导。与任何既有法律体系一样,自然人仍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最核心最根本的法律主体。自然人以外的法律主体和制度设计,都必须做事于人类的利益需求。
例如,国内外知识产权法学界正在热议机器人是否具有主体资格问题,如具有深度学习、思考和创造能力的机器人是否可以成为权利主体,授予其法律人格,从而使其能够享有著作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问题。譬如,英美等国家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法学家正在谈论能否授予机器人虚拟的法律人格。2016年欧盟委员会法律事务委员会向欧盟委员会动议,将最前辈的自动化机器人的身份定位为“电子人”,授予其特定权利责任。2017年沙特乃至石破天惊地付与智能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资格。但是,无论这些谈论和做法如何鼓噪,在以自然人为中央的制度设计框架之下,即便是须要拟制的人,如法人,归根结底都是人类的工具,终极都是自然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在人工智能时期,是否授予机器人以法律上的人格,也一定以是否为促进科技创新和家当发展所必需为根本标准。即便是授予机器人知识产权主体资格,也不过是借此更好地实现自然人的利益,使之成为更好实现人类利益的制度工具。
(作者:孔祥俊,系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凯原法学院院长、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研究院院长)
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转载请注明出处!















